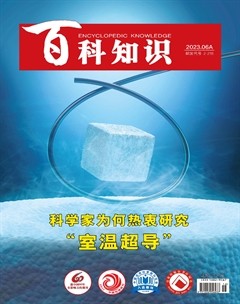春节刚过两个月,我国江南各地城市公园里的郁金香就已争先恐后地绽放。这是一种个头不高的观赏性花卉,它一株一花,绿叶肥大,主茎细长,花朵呈高脚杯状,花色艳丽,花香悠长,单株优雅高贵,连片绚烂如梦。我们的视线继续向东,韩国京畿道和日本富山县、新潟县等地的郁金香也都蜂飞蝶绕,引得游人流连忘返。跨越辽阔的太平洋,加拿大渥太华和美国新泽西州、密歇根州等北美多地也都于此时争相举办年度郁金香节。在欧洲,荷兰人将郁金香奉为“国花”;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也都不约而同地规模性栽种郁金香。人们对郁金香的日常性观赏和喜爱,激发了艺术家们以郁金香为对象的创作热情。在西方,梵高、塞尚、莫奈、马蒂斯、毕加索等顶级艺术家都曾在自己的画布上临摹过这春天的优雅花朵。
植物史学及相关研究成果显示,郁金香最早生活在中国与中亚接壤的天山山谷。8—9世纪,郁金香逐渐被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移栽和培育。自9世纪中期开始,郁金香不断出现在波斯诗人的诗篇里,为我们留下了早期郁金香盛放的画面。10世纪前后,郁金香成为波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宫廷皇室最喜欢的花卉。大约在16世纪,郁金香从奥斯曼土耳其传入欧洲。因为花形类似伊斯兰宗教人士戴的头巾,欧洲人便按波斯语的“Tülbent”(意为纱布做的头巾)的发音Tulip来命名这种来自东方的花朵。从17世纪开始,荷兰成为世界郁金香培育中心。也正是从这个时间开始,郁金香开始了自己的全球旅行。
同名异物,郁金香何时旅行中国
在中国,一提到郁金香,很多人会不由得吟出“诗仙”李白在《客中行》中的名句:“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既然“诗仙”都已经着墨,人们难免想当然地认为至少在唐代,郁金香就已经在中国大地开放了。但实际上,李白诗中的“郁金香”并不是我们今天在公园里见到的郁金香花,而是指“郁金”的“香”。郁金是一种中药材,为姜科姜黄属多年生植物,其根块可以入药,有保肝利胆、祛瘀止血的功效,也可以泡酒和染色。唐宋诗词中大量提及的郁金香多与此相关,如唐代诗人王绩在《过汉故城》诗中写道“清晨宝鼎食,闲夜郁金香”、杜牧在《偶呈郑先辈》诗中写道“不语亭亭俨薄妆,画裙双凤郁金香”,宋代婉约派词人晏几道在《浪淘沙·高阁对横塘》中吟诵“藕丝衫袖郁金香”等。

关于中国古代文献中的“郁金”,美国汉学家薛爱华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中写道:“虽然‘郁金’的名字里没有‘香’字,但是它和‘郁金香’还是常常混淆在一起。”的确,晚唐苏冕在《唐会要》中就有相关记载:“(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三月十一日……伽毗国(今克什米尔地区)献郁金香。叶似麦门,冬九月花开。状如芙蓉(花呈杯子状),其色紫碧,香闻数十步。华而不实,欲种取其根。”这段记载曾令很多学者产生误解,但仅从花期上我们就能判定该花是藏红花,其英文表述为Saffron,而不是Tulip。在古代文献中,也有把它翻译为“撒法兰”或者“茶矩摩香”的。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误解,首先与古代器物“同物异名”和“异物同名”的命名方式关系密切。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的人们出于各种原因,给相同的器物取不同的名字或给不同的器物起相同的名字的现象都相当常见,如中药材郁金和藏红花都被称为“郁金香”。其次,无论是“郁金”还是“郁金香”,都有“西来”的记载,这种地理上的重叠更容易让人们产生误解。如三国魏鱼豢在《魏略》中说“郁金生大秦国,二三月,花如红蓝,四五月采之香”,同时期的万震也在《南州异物志》中说“郁金香出罽宾国,色正黄,如芙蓉花里媆莲相似”。
为了表明中国古代文献中的“郁金香”与Tulip不是一类,美国历史学家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编》中甚至直接把文献中的“郁金”和“郁金香”放在了“红花和姜黄”这一篇章中进行对比研究。他明确指出:“‘郁金’有两种,一种是郁金香,只有它的花有用处;一种是郁金,只有根有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