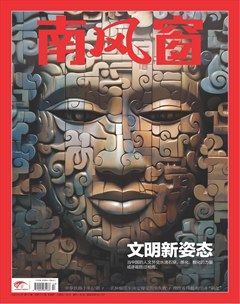哥伦布远航时应该也没想过,原本没有地理和文化联系的国家,有朝一日会被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商贸和人员往来的增加,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越来越靠近彼此,多元文化正成为大部分人需要面对的现实。当相互依存成为国际社会现状时,我们跨过了允许主权死亡的年代,开始正视文明共存的现实路径。
但差异、争端乃至热战并未就此削减,甚至有可能因文化误解和法律标准的不一致而愈显激烈。如何在“全球社会”这一集体框架之下,寻找一个“代价”更低、更有效率的争端解决方式,变得愈发重要。
过去,调解作为一种解决方案,被放置在争端解决的第三梯队。在更遵循个人主义的国度,人们更乐意采用诉讼或者仲裁来保障自身利益。只不过,无论是诉讼还是仲裁,都会花费当事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也很难在程序正义的框架下克服法律和文化方面的分歧。
在全球共同体意识更强的现今,调解机制正因其“东方智慧”而越来越受到关注。毕竟,并不基于法律前提,而更多基于沟通的调解,相对容易以低成本促成双赢局面。
调解理念在中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以和为贵”的价值取向和集体主义意识,共同将结果推演至此。作为社会权威的乡绅以“调解员”的角色出现在民间纷争之中的桥段,在古代中国已经上演了无数次。
惯性让现代中国仍保留着调解的文化因子,中国也乐于让调解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其应有的效力,同时承担大国责任。“国际调解院”就此应运而生。
2022年以来,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老挝、柬埔寨、塞尔维亚、白俄罗斯、苏丹、阿尔及利亚、吉布提等国共同签署了《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联合声明》,预备设立国际调解院这一国际组织,为解决全球争端出一份力。
当年10月,中国外交部与香港特区政府正式签署了《关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的安排》,预备将国际调解院设立在香港特区。
2023年2月16日,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正式落地香港,预备就《国际调解院公约》的国家间谈判及组织成立开展工作。待这一国际组织正式成立,筹备办公室或将转型为国际调解院的总部及秘书处,持续为世界各国服务。
届时,中国调解力量将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调解更具“人文关怀”
在中国决意设立国际调解院之前,国际社会已经看到了调解的潜力。为此,本是替代性解决方案的调解正逐渐得到各国青睐。相比对抗性更强的仲裁和诉讼,更低的成本、对差异的弥合以及私密性,成为了调解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
以仲裁为例,根据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数据,其平均仲裁费用已经超过11万美元,而平均仲裁时长则达到16.2个月。无独有偶,伦敦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费用中位数也达到近10万美元,而耗时中位数则为16个月。
相比之下,调解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都要少得多。国际商会仲裁院下设的调解机构在2020年的平均调解费用只达到2.5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