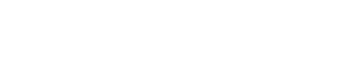今年3月,在一场关于儿童舒缓治疗的专家课上,我第一次见到了蒋轩竹,他是这场专家课的组织筹备者,同时他也是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一名医生。
我之所以对蒋轩竹产生兴趣,是由于他的医生身份很特别,其中容纳了两条看似完全相反的道路:一方面,他为儿童治疗血液肿瘤,竭尽全力让孩子的生命得以延续;另一方面,他为他们进行舒缓治疗,只为了让小孩体面地离开人间。
舒缓治疗即安宁疗护,是医学延伸向死亡而非延伸向生还的路途。
在很长时间里,像蒋轩竹一样的肿瘤医生,更多地被患者及家属寄予着妙手回春治愈疾病的厚望。哪怕病人最终生命垂危,也常常难以阻挡家属同病魔抗争的执着意念,直到最后时刻,也要切开气管维持呼吸,要按压胸膛挽留心跳。
但变化在暗自发生。与蒋轩竹类似的医生正在逐步成长起来,他们决定接受医学的有限性,当他们确定疾病已然很难再有治愈可能时,会采取主动的干预,引导患者和家属共同迎接患者生命的完结。
这并不是一场轻易的转变。存在于他们工作中的,是一种生与死不断拉扯的张力,人对生的渴望仍旧旺盛,对死的恐惧永远幽微。更何况,蒋轩竹面对的还是小孩,是最被期待的新生命。
就像是摸着石头过河,很多方法都未知而陌生。但他们正为此不断努力。
以下是蒋轩竹的讲述:
“就好像蛇杖一挥,世上就没有肺癌”
我出生并成长在台中市,小时候身体不太好,每当生病时,妈妈总是带我去我家对街的儿科诊所,找一位名叫林焰的医师看诊。
林医师是个慈祥的老伯伯。他出门诊是不穿白大褂的,他会戴一个工牌,穿西装,戴领带,当时他也挺大年纪了,头发花白。每次看诊,他都会很和善地摸摸我的头,跟我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完成查体,最后送我很可爱的贴纸,再交代我回家好好吃药。
有一次我妈妈对他说,其实你们可以准备一点巧克力糖或是饼干这些东西,小朋友会很喜欢。我很清楚地记得林医师说,我们尽量不给小朋友这些东西,是因为怕会呛到他们。因此我才发觉他已经体贴细致到这样的程度。
“你为什么要当医生?”
在小时候的某次看诊过程中,我曾问过林医师这个问题,他跟我说:“因为我很喜欢修理东西,你们的身体坏了来找我,我就可以帮你们修理好。”
其实我原本不是当医生的。曾经在高雄市读本科的时候,我读的是生物科技,那时候很不成熟,花光了爸爸给的零用钱,就只好自己去做兼职。
当时我还是没有放弃小时候很想要当医生的梦想,所以尽管我不是医学生,也还是去我们大学附属医院的急诊科找了一份兼职,当护工,就是去推病床、送病历,干这种体力活儿,一小时赚80块台币。
有次我去上大夜班的时候,就出车祸,我听到两辆120开车进来,送来了两团血肉模糊的生物体。
当时冲击很大,觉得很恐惧。因为你不懂,你只看到血肉模糊的画面。
那是一对小情侣,半夜两点多吃完宵夜之后去约会,在回程的路上被货柜车碾过去,男孩子当场就没了,女孩子进了抢救室,凌晨两点多钟来的,到大概七点半也不行了,也送进了地下室。
我对这个事情印象很深刻。我会觉得,如果我当时有足够的技能的话,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只推病床,还可以去帮忙他们多做一点事情?
就是因為这个契机,我才回去找我爸说,我还是很想当医生,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我爸说,你试试看能不能考大陆的医学院。然后我就过来了。
当了医生之后,我总是还会回想起那天晚上的场景,我会一直思考,如果某天我再遇上那样子的事情,我该做些什么。
后来当了医生之后,我总是还会回想起那天晚上的场景,我会一直思考,如果某天我再遇上那样子的事情,我该做些什么。我会把那天晚上的画面放出来,重新审视每一个细节。我终于开始搞懂他们在做什么,我还会想,这个地方说不定还可以这样子做,那个地方如果当时那样处理的话就好了。
但是,在我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之后,我发现,有些人你根本就救不活,有些病你根本就治不好。
我在大学读内科学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挺有意思的小插曲。
当时我们的教授在讲肺癌,他挺老的,已经五六十岁了,感觉学识很渊博。他在PPT上面放了很多肺癌的X光、CT,还有切出来一些大体的组织,整个黑黑的。他最后说,患者可能会呼吸衰竭,肺要大切。
重要的是,他一面给我们讲课一面抽烟。他说,你们知不知道抽烟的人罹患肺癌的概率比不抽烟的人高百分之多少?
紧接着,他把烟往天花板上一喷,然后把烟头丢在地上踩熄,对我们微笑了一下。
突然之间,我们全班感受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动。他传达给你的那种感觉,在当下理解起来好像就是说,你们只要好好学习,有天你就可以跳脱于这些规则之外,你可以用你的专业知识去解决它,哪怕你抽烟,你也再不用恐惧这些东西。
就好像我们手握阿斯克勒庇俄斯蛇杖(神医用以起死回生的灵物),蛇杖只要一挥,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肺癌。
但现在,我感觉我应该是曲解教授的笑容了。
在我自己工作几年后,我再回想起那一幕,我突然对我们教授那个笑容有种新的认识,我觉得他好像是在说:“跟你们讲这么多也没有用,反正也治不好,该抽烟还是抽。”
以前在课堂上,我们觉得他的笑容是一种很自信、很有力量、很有士气的微笑,现在回想起来,那个笑好像是很无奈的看清现实的那种苦笑。
“原来蛇杖挥动受限于诸多枷锁镣铐”
梦想被现实打碎的那天,我正在参加新生儿科的规培轮转,这件事大概发生在我规培一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当时我还是个很菜的新手。
那天的情况是这样,有位妈妈本来一直没有怀上小朋友,后来好不容易怀上了,还是去做的试管,而试管本来就不太稳定。孕期26周的时候,这位妈妈就宫缩了,只能把小朋友生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