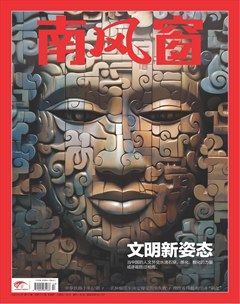文学院的张箭飞教授要退休了,今年是她最后一次讲《植物人类学》,等她退休之后,这门课程也会从武汉大学的课表消失。
有学生为此在学校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传到了社会上,也反响热烈。
这让张箭飞小小地“网红”了一把—出乎她的意料,她说,文学院、植物这些安静的事物,很少受到外面世界的关注。
张箭飞的家,对面就是武汉大学附属医院。2020年,疫情期间上网课的时候,她把教授的其中一门课改成了《瘟疫与文学》,学生们却显得不太有兴致。与之相对的是植物课班群的热闹,学生们把家中植物的照片发在群里,兴奋地讨论着花草的生长状态,甚至还有人把听课笔记画成了精致的手账。
人类与植物的紧密联系,在特殊的环境下重新显现。
物资匮乏的时候,每一根萝卜、每一颗大白菜都显得格外珍贵,没错,人们需要依靠植物获取生命的能量;疫情期间,许多人在家中研究自种蔬菜,土栽生菜,水培大蒜,智慧生物可以增加栖息环境的承载能力,这是人对植物的驯化。更别说植物大都长得美丽,茂叶丛花,环绕身侧,人的心情也会好起来。这些年,人们对于植物的兴趣似乎正在变得浓厚。
今年有另一件令张箭飞感到惊讶的事,作为一门文学院的选修课,《植物人类学》以前的学生顶多三四十个人,这学期选课人数却超过了一百。上课地点不得不从文学院改到了距离珞珈门更远的信息学部,只有那里有大教室。为此,不开车的张箭飞要特意走上20分钟。
不过也好,武大校园内树木遮天蔽日,经常有学生陪着张老师一起在这条路上来回,这是一段与植物相伴的路程。
一堂植物课
教室的投影幕布中,沾着水珠的白色栀子花缓缓开放。
“太性感了,”张箭飞发出感叹,“要是新娘穿上一套栀子花开的婚纱,简直美爆。”
5月下旬,杨梅、荔枝还没熟透,夏天刚刚开始,但大学的一个学期已经走向尾声。这学期《植物人类学》的倒数第二堂课上,张箭飞邀请了学生林翠云博士讲“香气”。

林翠云曾在巴黎拜师全球唯三的嗅觉文化学者,对香水颇有研究—这种从植物中提取出来的香气制品,在人类世界成为了权力与情欲的象征。
课上,林博士说了一个秘密:文学院一位中年男教授最钟爱的香水是阿玛尼寄情,用光了好几瓶,她揶揄道:他喜欢的都是“街香”。
听闻“秘密”,张箭飞笑:“我还以为本院男老师不会用香水呢。看来,我也有性别傲慢和嗅觉偏见。”
介绍到时下流行的BYREDO香水“无人区玫瑰”(ROSE OF NO MAN’S LAND)时,张箭飞说,这款香水应该翻译成“没有男人之地”,叫“女子学院”最好。
台下学生又笑。
今年是她最后一次讲《植物人类学》,等她退休之后,这门课程也会从武汉大学的课表消失。
早在2016年,张箭飞为英语系研究生开过一门《植物与文学》讨论课,后来改成《植物人类学》,“下沉”到对外汉语专业本科生培养方案。
张箭飞最初的想法很简单,没有人排斥植物,学生们如果以后在海外教授中国文化,讲植物是不会出错的选择。
香气是这门课的一部分,张箭飞自己讲课时,喜欢讲乡土植物,特别是乡土植物与民族记忆、文化认同的关系。开这门课之前,文学院里有一位老师研究方言的消失,张箭飞就想,乡土植物其实和方言一样,也在消失。
张箭飞研究的是景观与文学,当一个文学教授喜欢起植物,就会把植物也当作研究对象,比如她研究过原生于澳大利亚的桉树如何因为经济效益侵蚀了广西大片的原生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