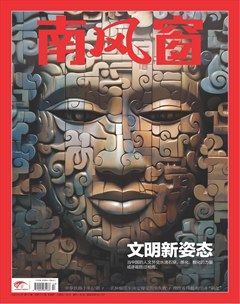《未来大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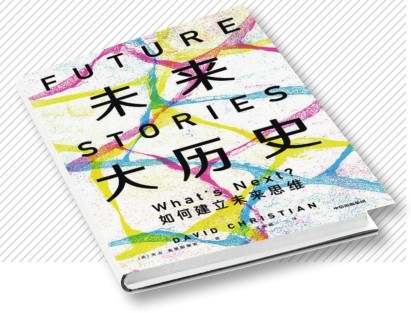
或许不少人都做过彩票中奖一夜暴富的“白日梦”,也都幻想过自己能够拥有特异功能,提前预知在未来开出的彩票号码。不过,现于悉尼麦考瑞大学任教的美国学者大卫·克里斯蒂安为这种想法泼了一头冷水:“想要弄懂未来可能有点像是想要抓住空气。”不过,这样的情况并不是没有好处:“生活中的戏剧性和兴奋感大多来自对未来的无知,而这也给了我们选择的自由,以及去深思熟虑的道德义务。”
或许,正是出于这种“道德义务”,大卫·克里斯蒂安撰写了《未来大历史:如何建立未来思维》。所谓“大历史”正是克里斯蒂安本人创造的名词,用以探索从宇宙大爆炸到现代的历史。
从学术意义上说,“大历史”是一个新兴领域,它使用多学科方法研究从宇宙大爆炸到现在的历史。研究“大历史”所需的“跨专业”特征,倒是正与大卫·克里斯蒂安的人生经历相符。他在牛津大学读博时学的是哲学,后来专攻俄国史,1984年还写过一本关于俄罗斯农民的历史著作,题为《面包和盐》。
为什么着眼“过去”的“大历史”会与“未来”联系起来?克里斯蒂安有自己的解释:“关于未来,我们仅有的线索都来自过去,这是最奇怪的一点。这解释了为什么生活会感觉像是一边盯着后视镜一边开赛车,也难怪我们有时候会撞车。”但也正是因为“我们也是在回望过去时步入了未来”,“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用过去照亮可能的未来”。
关于“可能的未来”,他给出了令人感觉有些沮丧的结论:“我们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基于“未来无法确知”这一前提,克里斯蒂安在书中给出了两个概念,“未来思维”与“未来管理”。前者用来囊括对于未来的各种各样的思考,后者则描述“那种试图把控或者按自己意愿调整未来走向的尝试”。
对于人类而言,“未来管理”又可以分为三个步骤:找到一个目标;寻找并分析所在环境里的趋势,搞清楚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然后行动,或者用书中的字眼,“下注”。这个词倒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古罗马的恺撒挥军渡过卢比孔河时所说的名言,“骰子已经掷下了(Alea iacta est)”。
这本书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描述单细胞微生物、多细胞微生物、植物以及动物的“未来思维”与“未来行为”。对于动物而言,这些功能是通过“神经元”实现的。譬如,果蝇的大脑里有差不多20万个神经元,而章鱼的神经元则多达5.5亿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