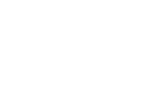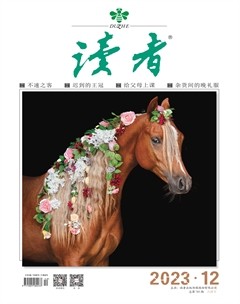我的未婚夫是一名在德国出生长大的德籍华人,他的父母20世纪80年代初来德国开设了自己的工厂,生意很成功。
记得第一次见他的母亲——齐耳短发,典雅熨帖,显出脸部线条的干净利落,身上有种女强人的疏离感。
说到发型,初到德国,最令我伤脑筋的就是找到一家心仪的理发店。我一家家试,最终找到了舒米。舒米是个五十岁左右的韩国女人,薄肩窄腰,略方的平板脸不失秀丽,有着亚洲女性特有的沉着干练。她嫁了德国人,但口音里仍充满浓郁的家乡调。
那日,我因要见一个重要的客户,便一早登门做头发。正做着,只见一个瘦削的男人提了只琴盒进来。他将琴盒扔在沙发上,对舒米说:“你的坏记性可别遗传给孩子们。”
男人离开后,舒米红着脸解释,那晚有一周一次的小提琴课,早上离家忘了带琴,托丈夫上班途中捎来。音乐老师是这条街上一家意大利餐馆的厨师,小提琴拉得很好。她给他免费理发,他教她小提琴。
这般年纪还学琴,我不由得对她刮目相看。她说:“儿子利恩德学了三年小提琴,自他第一次摸琴,我就跟着学,虽然学得慢,但从此家里有了音乐氛围。不过,我先生总觉得多此一举。”她笑了一下,自嘲道:“亚洲妈妈。”
在舒米那儿剪了三次头发,我萌生了一个念头:把留了十余年的直发烫卷。只因那天他母亲在看时装杂志时,对我微笑着说:“还是以前的人会弄头发,烫得优雅大方,现在的年轻女子都不讲究这些了。”
这话在我耳中盘桓不去。等她走开,我悄悄翻看那本杂志拍了照,对自己说:“要结婚了,换个发型也好。”
那天,我向舒米展示手机里的图片,说想尝试一下复古卷发。她略一踌躇,说可以做,但不保证和图片上一模一样。
我给她一个甜笑,表示相信她的手艺。我心情很好,讲起婚礼的筹备。她边剪边听,说:“女人呀,总是急着奔进婚姻,像到点就得吃饭一样,也不管自己饿不饿。以后有了孩子,一边上班一边肩负养育重任,遇上七年之痒,再赶上物价飞涨,那才晕头转向呢。”
女性的直觉让我担心起来,可别把我的头发做坏了——一个心情恶劣的厨师可做不出美馔。上卷发杠时,我试探着问道:“说起你丈夫,那天他绕路来送琴,是个暖男呢。”
她轻哼一声,说道:“他要是个暖男,也不会结婚纪念日带我去素食馆了!我知道他们家奉行素食主义,可孩子正在长身体,不能只吃素。更何况,那天是我们结婚十周年纪念日。”
我心生同情,但作为未婚人士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她。
她开始拆我头上的卷发杠,我闭上眼,幻想着未来婆婆那挑剔的双眼放出异光。
睁开眼,等等,这不是我许愿的礼物!“我要的是照片上那种自然优美的波浪卷,你看看这……”我两只手东拉一绺西拽一绺,急切地说,“这卷得跟弹簧似的,像个乡下老奶奶!”
舒米也感到很意外,脸上浮过一丝不安,强撑道:“刚烫完可能显得不够自然,相信我,两周后会更美。”
为了一场无瑕的华美婚礼,我把自己弄得殚精竭虑,可偏偏在婆婆重视的发型上出了岔子……我固执地认为,她因家事烦扰,心不在焉,毁了我的发型,都是她的错!
网页上,舒米的店铺下赫然出现了一条差评:“想见识因个人情绪而做坏顾客头发的理发师吗?欢迎登门!”即便她猜到是我写的又如何?反正不会再见。
转眼过了两个月,一头卷发慢慢养顺了眼。一日,因同事告病,上司临时派我前往科隆的国际会展中心。我想找人打理一下头发,结果家家都说客满——在德国,什么都须按预约来。
最后,我想到了舒米,她这个“工作狂”总是接急活儿。一番犹豫后,爱美之心使我放下了自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