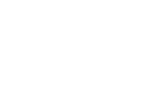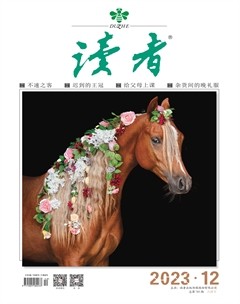1
1980年,我出生在吉林延边的小乡村,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3岁那年,刚进入腊月我就开始发烧。那个年代,像感冒发烧这样的小病全靠自己扛过去。
接连5天,我高烧不退,水米不进。我妈整日整夜地抱着我,用毛巾包着冰雪为我降温,但根本不管用。
村里的老人让家里人做好思想准备,说我这是被妖魔附了体。在农村,夭折的孩子是不能埋进祖坟的。所以,就连把我扔在哪道山岗,他们都替我父母选好了。
我妈不肯放弃。爷爷奶奶和爸爸拗不过她,只好拿出家里的最后一点钱请来神婆,给我叫魂。
钱花了,神婆请了,我却开始口吐白沫,脉搏也几乎摸不到了。
神婆开始推卸责任:“这是阎王定好的命数,谁也拉不回来。这孩子再不送走,全村人都会遭殃。”
爸爸、妈妈用新棉被将我包裹起来——这是他们能力范围内,为我进行的“厚葬”。
在山脚下,我妈流着泪对我爸说:“你在这儿等着,我想跟儿子再说几句话。”
我爸始终没等到我妈——我妈抱着我翻山越岭地逃走了。那一年,我妈26岁,到过最远的地方就是镇上。
2
从深夜到黎明,我妈只管朝最宽的路走。一路上,她逢人就问:“你们这儿有大夫吗?”
也不知到了哪个小镇,有人告诉她,镇上有个“药匣子”,平时就喜欢上山采草药,但老头儿性格古怪,很少给人看病。
我妈一路狂奔到“药匣子”家,二话不说就跪下磕头,求对方救她的儿子。“药匣子”被我妈吓到了,表示可以试试,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医死医活,她不可以跟外人说。
用药之前,“药匣子”对我妈说:“这孩子病得太重,狠病用猛药,就算救活,他将来是傻是呆,我都不能保证。”
我妈就说了一句话:“只要我儿子能活,不管是精是傻,我养他一辈子。”
汤药一点点喂进去,我妈不停地搓着我的手心和脚心。时间慢慢过去,终于,奇迹发生了——我的脉搏从弱到强,呼吸也均匀起来。我睁开了眼睛。
我妈号啕大哭,掏遍全身的口袋,也没摸出一分钱。她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拿起“药匣子”用来剪草药的剪子,将自己两条齐腰的麻花辫剪了下来。她恭敬地把辫子放在桌子上,然后抱着我转身离开了。
“药匣子”没有推辞,也没出门相送。
3
可想而知,我们母子平安归来,在村子里产生了多大的轰动。从此,村里的大人看到我,都会感慨:“你的小命可是你妈捡回来的。”
我妈从不说这句话,她精心照顾我的饮食起居,默默地观察我的一言一行。小学入学后的第一次数学考试我就考了100分,我妈一边往灶里加柴火,一边落泪。
那时候,我只觉得我妈跟别人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