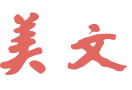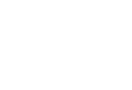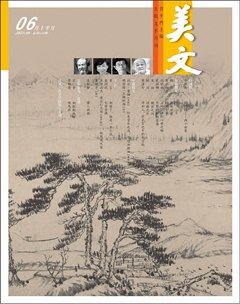无处不“儒” 无处不“道”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世说新语》)
子猷,何许人也,王羲之子,王献之兄。戴安道,即戴逵,画家。
明人陈继儒的评语:“古今二钝汉,袁安闭门,子猷返棹。底是避寒,作许题目。”即是说明是怕冷,却不明说,弯弯绕。
是耶?非耶?且戏为之“对号入座”。
“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再看《论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将其颠个过儿:“去远方访友,不亦乐乎?”
“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再看《老子》:“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儒家,道家,全在这儿了。儒家热肠,道家冷眼,一热一冷,反复相因,这表明了在现实生活中谁都离不开“儒”,也离不开“道”。读书人的活法是心热时就“儒”,心冷时就“道”。
子猷返棹,“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他说的“兴”,也就是《论语》中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乐”。可是,既有“来”,也就有“去”。有了“不亦乐乎?”也就有不“不亦乐乎”?《阅微草堂笔记》里有一扶乩故事,请仙降坛后,问:“弈竟无常胜法乎?”判曰:“无常胜法,而有常不负法,不弈则不负矣。”以弈之胜负比之朋友之聚散,则曰:不“聚”,则无“散”矣。既如此,相见真如不见,何必见戴。
“春秋”梢公唱“唐”诗
《楚昭公疏者下船》杂剧有梢公歌: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春秋时期的梢公唱起唐诗来了。岂料刚唱了两句,瞅见了船舱里的老婆孩子,唱词拐了弯儿:“也弗只是我里梢公、梢婆两个,倒有五男二女团圆。”一个孩子要撒尿,把其他孩子也给带累醒了,梢公又叹声唱道:“一个尿出子,六个弗得眠。”忽而如有所悟,大声吆喝起来:“七个一齐尿出子,艎板底下好撑船!”即兴生情,顺水推舟“一撑撑到姑苏城外寒山寺,”与唐诗又接上碴口了,“夜半钟声到客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