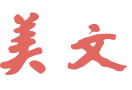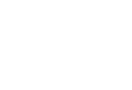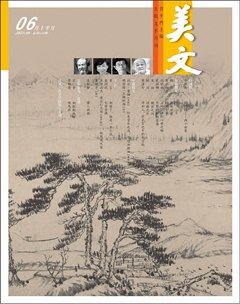糯米制品
过了元旦,离春节还有个把月时间,按照故乡的年俗,就到了该准备糯米团子的时候了。说到糯米团子,鼻子四周就氤氲着挥之不去的糯米味道。我迷恋糯米的香味,但不知何故却并不喜欢糯米做的糕团,这可能跟儿时留下的记忆有关。计划经济时期,制作过年时享用的糯米糕团,对我们常州人来说可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别的不说,光就着石磨磨米粉就是一桩耐心、气力、技巧一样都不可或缺的勾当。记得有一年寒假,我曾经在外婆家自告奋勇帮外婆磨粉,因为完全不懂技巧,只会用蛮力,结果半天下来,握着磨盘把手的手指磨出了水泡,从胳膊到背到腰几乎没有一处不酸、不痛,至今回忆起来仍然心有余悸。可能是从小留下的心理阴影吧,我对所有过度加工的糯米制品都抱着一种敌意,觉得它们是对“大道至简”这一人生哲理的反动和嘲弄,职是之故,在我心目中最迷人可口的糯米制品,不是那些工艺繁复、内容芜杂、色彩瑰丽的糕团,而是我母亲用糯米粉调制的“无米粥”。每逢节庆日子,大鱼大肉吃过,老妈总是不声不响用冷水兑上一碗糯米粉,细细调匀后倒入沸水锅中,只需筷子在锅中搅拌几下,一锅奇香扑鼻的糊状“无米粥”就大功告成了。端上桌来,稀里哗啦一碗下肚,顿觉通体舒坦,所有油腻肚胀感被扼杀于萌芽状态。“无米粥”贵在无米,如果米糊中杂以米粒,则又是另外一样东西了。现在常州的快餐店里常备有免费的米糊,惜乎过稀,且没有糯米特有的香味,让人不免产生好事没有做到底之感,不过,如此贴心的服务,除了全民贪吃的吾乡,恐怕也没有第二个地方做得到了。
面 条
这几年,江南面条已成贪吃界新宠,朋友圈里人人都在大赞苏州面条(其实常州面条的奇技淫巧并不比苏州差到哪里去)。个人感觉,这些面条写在纸上时都比盛在碗里好吃,其主要原因就是——温度。一碗好面,写在纸上时可以完全忽略温度的因素,但是送进嘴里就必须正视温度差异带来的不同口感了。现在苏州和常州大部分面店的问题,就是面虽现下,但浇头都是早就备好的,面端上桌时虽然热得烫嘴,但是只要冷冰冰的浇头放进面汤中,立即中和了面汤的热度,热面汤瞬间变成温吞水,这面也就吃得不上不下了。所以,如果确定浇头不热(焖肉、熏鱼、大肠、鳝丝这类常规浇头很少有滚烫的),建议还是“过桥”,切勿胡子眉毛一把抓,把好端端一碗山清水秀的细面弄成十三不靠的大杂烩。我们常州有一家号称有百年历史的义隆素菜馆,面条一般,但是现炒的浇头极好,印象比较深的有用魔芋仿制的虾仁、用香菇丝仿制的炒鳝丝,也不知道用素油炒出来的菜是怎么产生那种活色生香、裙裾摇曳的人间烟火气的,常有人用“几可乱真”来形容素菜馆仿荤菜的好,但是这种修饰手段用在义隆身上不妥,也不确,因为义隆的“李鬼”比李逵本尊更像“黑旋风”,对味蕾的蛊惑力和杀伤力更大,简言之,就是义隆的假虾仁比绝大多数餐馆的真虾仁更好吃。把刚刚出锅的假虾仁、假鳝丝拨一点在同样刚刚从面锅中捞出来、滗掉了汤水后略带一点碱味的细面上,拌一拌后入口,那种干柴烈火碰撞出来的真滋味会撕碎所有肉食者对于素菜的狂悖想象。因之,义隆素菜馆也成为我这个无肉不欢者每次回乡必欲打卡的圣地之一,不过,这种朝拜已经跟面条没啥关系了。
大 肠
几乎找不到任何一样别的食材能像猪大肠一样把三观、性情、背景大相径庭,甚至针锋相对的人拢在一起兴风作浪了。大肠的好无需多言,就说一句:这个神一般的存在,在我看来证明了至少一个真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换句话说,就是“野百合也有春天”,同時也证伪了至少一个歪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大肠当然是“民族”到极致的物事,可它跟“世界”没半毛钱关系,除中国人以外的“世界人民”从来就不尿大肠这一壶。西班牙以伊比利亚黑猪肉名世,西班牙人对猪肉的热爱比起中国人来不遑多让,甚至有些地方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对火腿的种种吹毛求疵,但大多数西班牙人除了吃灌肠、血肠外,对纯粹的猪大肠无感,西班牙的菜场、生鲜超市基本看不到大肠的身影,两个猪肉食用大国在对待猪大肠的问题上形成了鲜明的两种观点、两个流派,相比之下,个人觉得吾国对于大肠的怜惜和热爱更接地气,也更符合我们这个曾经长期吃不饱饭的苦难之国的国情。常州人通常把猪大肠叫“肠肠”,有一种大人呼唤自己孩子的亲切和默契,而且,只有猪大肠可以享受这个待遇——鸡肠、鸭肠、鹅肠,是不能以“肠肠”二字呼之的。由此可见,常州人跟猪大肠之间早就建立了外人难以一窥堂奥、一探究竟的暧昧关系。关于猪大肠的做法,吾国的各大菜系都有自己的绝活——红烧、爆炒、九转、脆皮、双臭。个人感觉,大道至简,还是红烧最能把大肠那种不可言说的销魂感表达得畅快、清晰,也只有红烧能撇开各种配料的羁绊和拉扯,把大肠特有的暧昧味道在火的锻打、洗礼下变成吃货们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召集令和密电码。当然,即使是红烧,各地的做法也不一样,有的地方会放青椒片,有的地方会加大量蒜瓣,吾乡的做法是除了葱姜、料酒、酱油、少量八角和砂糖之外什么都不放,纯靠火功正面强攻。这很考验厨师的功夫。火候、咸与甜的拿捏尺度,端赖经验和悟性,那些教做菜的小视频是教不出来的。一锅成功的红烧大肠是完全可以用“风骚入骨”四个字来形容的。卖相、气息、质感、味道,无一不增之一分则长、去之一分则短,这样的大肠可能在常州普通人家出现的概率要比饭店酒家高得多,盖因家庭主妇对整治大肠的手段已经形成肌肉记忆,心到手到,不易翻车,而正儿八经的厨师则因为要照顾的环节太多,经常顾此失彼,反而容易失手,所以,想要吃到让人梦牵魂萦的好大肠,去饭店可能会是一场冒险。不过也有例外,吾友小宝开的小馆子玺舍有一道众人都说好的“拿魂菜”——土匪腰花肥肠。主料是大肠和腰花,配料是黄瓜片、芦蒿(或芹菜梗)、洋葱、油渣,看起来主配料有点十三不靠,我想这可能正是厨师冠之以“土匪”之名的原因。但是细想起来,这种搭配其实非常科学:两位主角都是蛮横桀骜的主,理应由黄瓜、芦蒿、芹菜这样的清纯之物来降一降火;洋葱则可以起到合纵连横的作用,稍微制衡一下大肠、腰花的味道后把黄瓜、芦蒿、芹菜的热情激发出来,并且在口感上增加层次;油渣则最后奠定了这道菜与重口味爱好者们眉来眼去的最后基调。需要强调的是,这道菜一定要在上桌十分钟之内解决战斗,菜温一降下来,就不是那个味道了。
咸鸭蛋
汪曾祺笔下的咸鸭蛋实在令人心驰神往。窃以为,在全世界最好吃的东西中,腌得恰到好处的新鲜咸鸭蛋黄(不包括白)可以排进前五(只是个人感觉,不争论)。但是咸鸭蛋品种太多,良莠不齐,所以对咸鸭蛋的观感确实不能强求统一。汪老的家乡高邮以出好鸭蛋闻名于世,我吃过真正的高邮咸鸭蛋,是朋友家自己腌的,那一个“好”字实在不是文字所能形容。但是好咸鸭蛋并非唾手可得,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不可缺。地利人和不必说,就说天时:鸭蛋腌制的时间不够,则蛋黄出油不够,咸鸭蛋尚未破茧成蛹,味道大打折扣;腌制时间太长,则蛋白就会变咸,而且越来越咸,白和黄形同陌路,更不用说坐收珠联璧合之效了。早不得、晚不得,究竟何时瓜熟蒂落,端赖腌蛋者凭经验和感觉运筹帷幄。但经验和感觉也并不百分之百可靠。我吃过同一朋友前后三次送的咸鸭蛋,第一次极好,第二第三次就稍逊了——腌的时间长了点,蛋白已不可入口。所以,说到咸鸭蛋,并非冠以“高邮”二字便足可保证质量,里面的讲究多矣。现在市面上有标示高邮出产的小包装熟咸鸭蛋,开袋即食,打开后蛋黄也油得有模有样,但味同嚼蜡,高邮蛋之形尚在,神则脚底抹油,早溜得无影无踪了。我的故乡常州并不以咸鸭蛋称誉江湖,但是近些年给我留下印象的好鸭蛋,似乎都是在常州吃到的。常州人家,平常日子在饭桌上备三五个煮熟的咸鸭蛋已经成了家庭主妇们心照不宣的“自发秩序”。这些鸭蛋大都出自附近菜场,因为做的都是熟客生意,主顾间知根知底,所以鸭蛋的品质是不用怀疑的。我总结了一下这些鸭蛋的共同特性,大约有以下几点:(1)均为粽叶水所煮,蛋白略呈浅黄色,不咸,可以大口吞吃;(2)蛋黄颜色很深,但并不很油,吃在嘴里有沙粒感,有一种特异的浓香,完全没有通常情况下鸭蛋难免的腥味;(3)可在常温下放置三天左右,三天以后,蛋白开始收缩,蛋黄也慢慢失却神采,而且变咸,口感大受折损。在我看来,常州的这些在小菜场随处可见,并不十分起眼的咸鸭蛋,已是我们目前在市场上能够邂逅的性价比最高的咸鸭蛋了。不过话说回来,真正好吃的咸鸭蛋,还是得自己在家煮,那种出锅不久,还带着余温的好咸鸭蛋,一口一个,两三个下去,直能叫人目瞪口呆、魂飞魄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