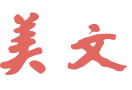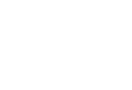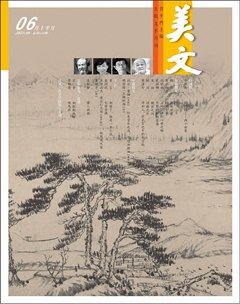一
“头发对于凡一平真是多余之物。”
接着我又想:“他要头发有什么用呢?打理起来多麻烦啊,哪怕一根他都不需要!”他白而胖的脸长得圆润周正,最是符合老一辈人天圆地方的审美标准,是吉人的天象;光洁宽阔的脑门寸草不生,也应了人们惯常的认知里,面慈心善又功力非凡的高僧大德印象;当然还有另一说,聪明的脑袋不长毛,这或许更多是他自己的称许和暗示。单有这光洁硕大的脑袋倒没什么值得称奇的,关键是光芒万丈的脑门与气势恢弘壮硕的身材相得益彰,哪怕是第一次见面,都不得不连呼他的面容与身材真是天造一对地设一双的高度和谐呀。反正这样的形象已深入人心,家人习惯了他这个模样,朋友喜欢他这个模样,文坛甚至需要他这个模样。否则,哪天他长出浓密的头发练出挺拔的身姿,去开个读者见面会什么的,只怕会吓着那些千里追星的迷妹们。
迄今为止,他已出版长篇十部,小说集十二部。他创作的速度与数量,震惊到令人头皮发麻语无伦次词不达意之境。反正他一边喝着酒吃着肉还能一边写小说就对了。他隔三岔五发的朋友圈,要么是自己的新书发布会研讨会,要么是某一新作被谁转载了,哪个小说又上了某某排行榜,再就是花花绿绿的书画作品。近年他习书作画,不久前还出版了本新的书画作品集。据说他的画相当的有市场,我是说不仅仅是以画换酒吃肉的那种。由他的同名小说改编成的电影《寻枪》《理发师》传播深远。尤其是2002年,他的《寻枪》横空出世,创下了当年票房第一的成绩。总之他是个编织故事的高手,他的小说不断地“触电”,因为他作品的故事框架和人物框架有足够的精彩和二度创作的情节空间。在广西的小说作家里,他作品中那种带“静电”的叙述感总是很强。
凡一平的影响力有目共睹。接下来的日子,这辆重型创作快车是否提速不得而知,但保持当下的车速不容置疑,这都得费多少脑筋啊。要是有一头的秀发,肯定得跟他小说里的人物或者故事抢食不是?一个人的头目脑髓大概是固定了的,尤其到了这个年纪,要真得到神的加持,还真不会有多少扩容的空间,何况神助的可能性不大呢。再说,凡一平为群居性特征明显的代表人物,他喜欢热闹喜欢呼朋唤友,偶尔有特殊的宾客,他甚至会连轴赶场,一顿两餐大酒。但酒足饭饱酒酣耳热之后,回到电脑前立刻判若两人。我想,写小说及喝酒作画之外费时费力的事,估计凡一平一件都不愿做。常常他的写作状态是这样的,晚上跟朋友喝完一餐偶尔两餐大酒,凌晨回到家中,看完母亲睡前留下的字条“水果已洗好,回家记得吃”,坐在茶几前发了一会儿呆,吃了九十岁老母亲洗切好置于桌上的水果,再走到书桌前打开电脑。
二
不知道他的头发都到哪去了,写小说熬夜熬的?当然不是,这个是可以肯定的。似乎从认识的第一天起,他就顶着个圆润而亮堂的脑袋。第一次见面是1996年的岁末,那一年的七月我刚从《南方文坛》调到《广西文学》,杂志社最是兵强马壮的时候,社长蒋锡元和主编罗传洲是被称为史上最强拍档的两位老总。那年头的全面改革正好落到文学期刊的头上,说是文学刊物不再有财政拨款,不管是纯文学也好高雅艺术也罢,都得走市场。一时间,人人都有了山雨欲来的岌岌可危,甚至有人喊道“狼来了”。这样的大环境,文学自然也由八十年代的鼎盛繁华渐渐地过度为门前的冷落。两位老总在业内却能叱咤风云,坊间就有诸多关于他俩的传说。由杂志社主导张罗的“1996全国省级文学期刊生存与发展研讨会”,几乎把大半个中国30多家文学期刊的老总都召集到了广西,《大家》创始人李巍、《北京文学》兴安、《小说家》闻树国、《钟山》赵本夫及徐兆怀、《山花》何锐、《雨花》姜琍敏以及《小说选刊》冯敏和《小说月报》刘书棋等都悉数到场。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唐达成专门致信会议,充分肯定会议的意义。刊物被断奶,文学即将遭遇市场的预判,会上自然是一片的唏嘘感叹。记得当时已是名满诗坛的广西籍诗人杨克,以副主编的身份代表广东的《作品》出席会议,他那张标志性娃娃脸乌云密布,不无忧虑地说,一面编稿一面找钱出刊的难度肉眼可见,想想还有二十年才能退休,真是件可怕的事情。可会后这些以办刊为业的编辑老总们,又把“生存与发展”的时艰忘得一干二净,会议期间的空隙,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谈的还是文学。记得离会的前一晚,聊到凌晨大家依然意犹未尽,也不知谁提议吃宵夜,呼啦啦一干人马立即响应。结果是坐了五元钱路边的三轮车到夜市,只吃了碗两元的汤圆。应该算是史上车费比餐费贵的一次宵夜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因风云激荡的经济改革建设,曾经如日中天的文学,慢慢回落到它正常的状态。这样极大落差的初期,经历过文学繁盛的道行中人多有不适,社会对于文学的崇尚也日落西山。不曾料到,在几乎人人经商而文學落魄之时,这世上还有不为社会风向所动的金角落,会议结束后的第二个周末,都安瑶族自治县的广播局局长潘红日,也就是后来拿了骏马奖的红日,邀请《广西文学》到都安举办文学创作基地挂牌仪式。这是我自毕业后迎来的第一个基层邀请的文学活动,也不得不感叹低迷时局之下的都安文学热情。《广西文学》年办刊经费曾经连续多年缩减至六万元,还有几十万元的办刊差额都由蒋社长和罗主编通过自身人脉及举办活动得以补缺。事实是,文学之火虽已不是之前的高蹈火焰,它的持续与恒常却是始终不渝的。二十多年过后,断奶的“狼”在各地各有所异。在南方,杨克把《作品》经营得有声有色,文学走到今天依然坚挺。甚至迎来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绕了那么个大圈聊文坛轶事,实际是为第一次与凡一平会面提供背景。红日同时也邀请了都安籍的《三月三》编辑凡一平。那会儿他刚从复旦进修回来,大伙欣喜地看到,他的创作热情似乎跟当下日趋沉寂的文学时局背道而驰。那时搞文学多少有些灰头土脸的,稿源大不如前。传洲主编严肃地说,作者读者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这个时代还有人读小说爱文学,我们的工作才有价值。他给都安和凡一平都竖起了大拇指,说,了不起。
到都安出发前已临近中午,大家一合计都说吃过午饭再走吧。车子出了城不久,便拐到武鸣方向高峰林场的甘家界柠檬鸭总店。我有羽毛恐惧症,但凡餐桌上有羽毛的都不敢动筷子。可除了我,一车的人都说要吃柠檬鸭,我便不好做声。担心这客观事实一旦说出口来,会不会成了非分要求,进而断了他人的口福毁了别人的美好时光?正是年终岁末,平日里大伙都难得集体出城吃个饭,又遇上这么风味独特的餐馆,还都嚷嚷着说来两份大盘柠檬鸭,甚至叫嚣,今天单吃这鸭子,吃个够,其他不点了。一看这情形实在架不住,我才着急,赶紧说汤和青菜都还没呢,上个车螺芥菜汤吧。等一顿饭吃下来,大伙才发现,世上竟还有这般离奇到不可理喻的恐惧症。
凡一平对我的“不好意思”很是疑惑费解,大概率他将此解读为女生成不了大气的拘谨扭捏。摸着自己圆润的脑袋看都不看我一眼,很不屑地说,刚才大家讨论吃什么你怎么不作声?类似的事情,以后你不说就没有饭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