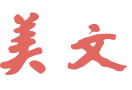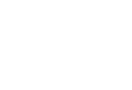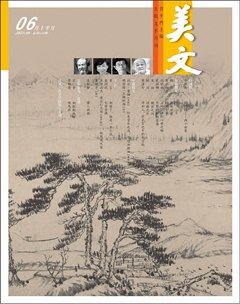沿奥卡河①旅行
沿着俄罗斯中部的乡间路旅行,你就开始明白俄罗斯乡间为何会有如此令人舒缓的作用。
这是因为它的教堂。那些教堂拔地而起,高度超越了山岭和山坡,犹如红色与白色的公主从高处走下来,前往宽阔的河流,钟楼显得纤细,上面有雕刻和回纹饰,高耸于人们日常生活的茅草小屋和木头棚屋之上。从大老远,它们相互致意,从遥远的地方朝着同一片天空耸立而起。
你可以到处漫游,越过田野或牧草地,远离任何一个家园,你从不孤独:在树墙之上,在干草垛之上,甚至在地球的曲率本身之上,钟楼的圆顶始终在召唤你,从波尔基②、洛维茨基、柳比奇或者加夫里洛夫斯科召唤你。
然而,当你进入一个村庄,你就意识到那些从大老远就欢迎你的教堂不再活着。它们的十字架早已弯下了腰,或者断裂;油漆剥落的圆顶露出锈迹斑斑的胸廓;屋顶上和墙缝中野草丛生;墓园几乎荒芜,十字架东倒西歪,坟墓遭到洗劫;祭坛后面的圣像历经十年风雨,已经褪色,上面布满猥亵的涂鸦。
门廊上有一桶桶盐,一辆拖拉机突然掉头朝它们驶去,或者一辆大货车朝小礼拜室的门倒退,装载一些麻袋。一座教堂中,机床轰鸣作响;一座教堂沉寂无声地矗立,只是被锁了起来。其他教堂变成了俱乐部,举行宣传会(“我们将实现牛奶高产!”)或者放映电影:《海洋之诗》《伟大的历险》。
人们总是自私,常常还邪恶。但三钟经③的鸣钟一度时常敲响,回音越过村庄、田野和树林而飘荡。它提醒人必须放弃尘世的杂念,把一个小时的思想赋予永恒的生命。那如今对于我们仅仅残存在流行歌曲中的晚钟的鸣响,把人提升到超越野兽的层面。
我们的祖先把最好的东西放进了这些石头和这些钟楼——他们所有的知识,还有他们所有的信念。
维特卡,赶快振作起来,别再垂头丧气!电影在六点开演,舞会在八点……
在叶赛宁④的故乡
沿着道路,四个单调的村庄一一展开。灰尘。没有花园,附近也没有树林。东倒西歪的围栏。到处都是某种漆得俗丽的百叶窗。道路中央,一只猪在水泵上擦痒。当一辆自行车的影子飞快掠过一群鱼贯而行的鹅,那些鹅便一齐转动脑袋,对着那个影子欢快地发出侵略性的鸣叫。在路面上和院子中,一些鸡忙碌地抓扒、觅食。
即便是康斯坦丁诺沃⑤的乡村杂货店,看起来也像快要散架的鸡窝。腌制的鲱鱼。几种牌子的伏特加。人们在十八年前就不吃了的一种黏糊糊的硬糖果。一条条圆滚滚的黑面包,是你在城里购买的面包的两倍重,看起来,仿佛命中注定要用斧子去劈开,而不是用刀子去切开它们。
在叶赛宁一家的村舍里面,可怜的小隔板还不及天花板高,把里面分隔成更像是橱柜或者单厩间,而不是房间。外面是一个栅栏围住的小院,这里曾经有一间浴室,在这里,謝尔盖⑥会把自己关在黑暗中写最初的那些诗篇。栅栏那边,是常见的那种牧马用的小围场。
我围绕这个村庄漫步,这里跟其他那么多的村庄并无二致,村民主要关心的依然是庄稼收成,怎样挣钱,怎样跟邻居往来,而我所感动的是:神圣的火焰曾经烧灼到这片乡间,我至今还能感到它在烧灼我的面颊。沿着陡峭的奥卡河岸一路前行,我惊奇地凝视远方——难道那里真的是那片遥远而狭长的赫沃罗斯托夫树林⑦,它曾经激发出这一唤起回忆的诗句:
“森林吵嚷着松鸡的悲叹……”
这就是同样宁静的奥卡河,穿过浸水草甸而蜿蜒流淌,他对此这样写道:
“太阳的草垛堆积在水的深处……”
造物主肯定把何等的雷霆猛掷到了那座村舍之中,猛掷到了那个性急的少年心中,因为雷霆的冲击,让他睁开眼睛看见那么多的美——在火炉边、在猪圈里、在打谷场上、在田野中——那千年来仅仅被其他人践踏且忽视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