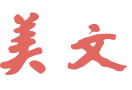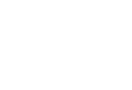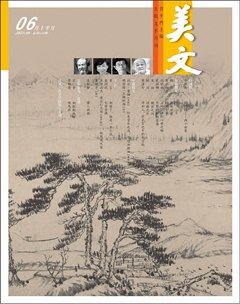终于,高长子落笔了,缓缓写下几个字,用的正楷。他一个字一个字写,我一个字一个字念,当然念得很慢:
无根而固者,情也。
大约是个初春的上午,因为家中院子里的玉兰花树结苞了。我去巷口的自来水站挑水,远远看见有个瘦高男人,很深地弯下腰去,跟收水筹的吴三婆婆问话。吴三婆婆坐在板凳上,见我挑着水桶走近,便朝我一指,对那人说,他就是王霈的满崽。又大声说,王霈被抓走了呵!
我不作声,随手将水筹递给吴三婆婆,兀自拧开龙头接水。待两桶水放满,挂好扁担钩准备起肩,那瘦高男人却将我轻轻拨开,说,你带路,我来。说罢,轻轻松松提起两桶水,低头看着我。我看他一眼,穿件褪了色的蓝布解放装,且闻到隐隐的有股汗酸气味。
我背起空扁担,在前头走。他在后头问我,好多岁了?我仍不吱声。他只好自语道,你大哥,应该有二十出头了。
刚进大门,正好碰见母亲在扫院子,一眼,彼此就认出来对方。
淑君!他叫母亲。
高长子?母亲叫他,这显然是叫外号。
我按雨苍信上的地址找来的,那高长子说。你们住的这地名古怪,倒脱靴。也难得找!母亲一愣,说,雨苍最近给你写了信?高长子立时明白了母亲的意思,说,没有没有,我是按先前信封上的地址找来的。
母亲这才释然。说,你不是在南京吗?高长子淡淡一笑,说,回来大半年了。
我未曾料到此人竟然叫父亲作雨苍。父亲名霈,字雨苍,是祖父起的名字,因为八字缺水。先前只有母亲才这样叫。但听到一个不认识的人也这样叫,覺得有些古怪,不好接受。
我看看母亲,她倒显得自然。
就这样,我头次见到了既姓高,个子果然也高的高长子。后来知道,他与父亲都是长沙人,抗战期间又是重庆中央政治大学的同学,毕业后又同在重庆盐务局供职。直至抗战胜利后各奔东西,从此再也不曾晤面,仅偶有书信来往。待到我认识时,他已近天命之年。
而那年的我,大约十三四岁的样子吧。
那日,高长子跟母亲在屋里说了好久的话。我坐在院子里的阶基上翻一本破小人书。忽然听见屋里传来母亲的笑声,很意外。好久没听见母亲那样大声笑过了。
母亲八十六岁那年,曾应父亲另一位在台湾的政大老同学之约,写过一篇很短的回忆文字,其中忆及了重庆的那段生活:
“……六十年前辞去已四年多的教学工作(语文、音乐、体育、美术),带着五岁的孩子,从湘西凤凰步行到辰溪,搭往贵阳的货车,转至重庆。四月八号动身,路遇暴风雨加大冰雹,雨伞吹翻。到重庆,王霈已在盐务局工作,后调南温泉。政大十期同学又同事,常来我家聚餐,都喜欢吃我做的菜,尤其是盐菜扣肉。又玩牌,外游花滩溪。有次到政大,正遇到蒋校长在大礼堂训话。散会后我们都跑到大路边,看蒋校长神气地走过。南温泉有一座大山流出两条溪水,一条是凉水,我家住凉水沟,一条是温水,附近人家去洗衣……”
其中提到的蒋校长,即蒋介石。
在这段短短的回忆中,母亲并未具体提及某个同学的名字。但我想,政大十期的“同学又同事”里,高长子必定是其中之一吧。
父亲毕业后,抗战尚未结束,不少同学都留在了重庆。高长子与父亲在重庆盐务局同事时,主要负责“计口授盐”的工作。我问过高长子,什么是“计口授盐”。高长子告诉我,抗战时期,四川及边缘省份食盐供应紧张,且有奸商囤积居奇,牟取暴利,政府只得按每户人口多少来分配食盐。重庆因贵为陪都,每人每月一斤二两,其他市县每人每月一斤,但凭购盐证到官盐店里购买。
我便插嘴道,还是新社会好,买盐不要证。高长子却似笑非笑地说,如今有粮证,还有粮票啊。我想也是,有点不好意思。
高长子又说,抗战后期,重庆国民政府关于计口授盐的具体谋划,以父亲与他为主。但大至调查报告,小至购盐证之设计,都由父亲执笔。这样一说,母亲也记起来一些细节。说那张购盐证是淡黄色纸印的,每户一份,每份十二联,每个月只能撕一联,当月用当月的,不过也够了。那时一家四口人(后来又生了姐姐),每个月有将近五斤盐,并吃不完。后来还攒下几斤,腌了些盐菜。高长子便趁势说,在重庆时,你做的盐菜扣肉,实在好吃!
此后,高长子便经常来倒脱靴看母亲了。开头两回是空手来,后来每次几乎都带点吃的。母亲先是推辞,但看看站在旁边瘦小的我,只好无奈收下。高长子于是松了口气,说,不要介意,反正我如今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但我发现,高长子从来不提及父亲的近况,母亲亦从不过问高长子为何从南京回了长沙。两个人似乎都心照不宣。只有一回,高长子背了一小袋米进屋,母亲便问,如今你在长沙到底做什么事?高长子轻描淡写地回答,给一家街道工厂做会计。见母亲有些狐疑地打量他,高长子拍拍胸脯,说,给小工厂当小会计,小菜一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