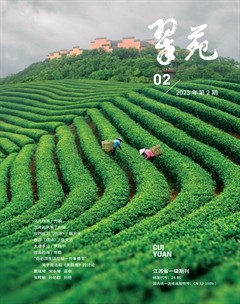我老家所在的绍兴市越城区富盛镇乌石村,是鲁迅先生短篇小说《祝福》中“阿毛”的原型地。据说,鲁迅先生家的祖坟,在我们村边上的调马场村(后与青塘村合并,现名“青马村”)。那个村是山村,不通水路。鲁迅先生小时候,他家来上坟,要先摇船到我们村,然后上岸,走路去那个村。当时,我们村的土地庙香火鼎盛,逢年过节都要演社戏。因为戏台就在岸边,鲁迅先生他们就待在船上观看。有一年,我们村有个小孩,一个人在弄堂口剥毛豆,被后面田畈过来的一只毛熊(我老家对“狼”的称谓)给叼走了。鲁迅先生听说了这事,记在了心里,成年后,写进了短篇小说《祝福》里。
这个故事,在我孩提时代,听父亲讲过。不过,不太听得懂,只记住了有个写文章的人叫“鲁迅”;也因为那个被狼叼走的小孩家所在的弄堂,就在我家那排楼屋最右侧处,由于通向广阔的田畈,夏天风很大,颇为凉快,我们常坐在那里,编麦秆扇(赚手工费,补贴家用),所以我时不时会想起那个被狼叼走的孩子。后来,1999年左右,我获赠绍兴市文联主编的一套书,其中有一本中写到了这桩轶事,而且比父亲讲的更详细,还写到鲁迅先生小时候与他的弟弟周作人,经常一道去踏看同样在我们村的“跳山大吉碑”(正式名称“建初买地摩崖石刻”,现为“全国文保单位”,我父亲在世时,被聘为业余文保员,曾悉心看护十多年)。
鉴于这层关系,我读中学时,接触到鲁迅先生的作品,感到特别亲切,没有其他作家所说的“违和感”。当然,这也许跟我与鲁迅先生同为绍兴人,语言上没有隔阂(不存在看不懂这个问题),有一定的关系。还有一个因素,我们高二上学期的语文老师董铭杰先生,毕业于浙江师范学院(现在的“浙师大”),本身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他后来为我兼任执行主编的一本杂志写过好几年稿,直至病逝为止),他对鲁迅先生作品的讲解,有别于其他语文老师,精彩、生动、风趣,使我从此爱上了鲁迅先生的小说,并激发了对写作的莫大兴趣,立志成为一名作家。
高中毕业后,我业余从事文学创作,特别希望成为鲁迅先生那类作家。受这种欲望的强烈驱使,我有意识地阅读了大量外国现实批判主义作家的经典作品,像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巴尔扎克等的中短篇小说。然而,由于受鉴赏水平的局限,虽然偏爱鲁迅先生的小说,基本上每篇都反复诵读,但事实上并未真正领悟其含义,只是拙劣地学了一些批判的手法,运用到正在创作的微型小说中,像《抢来的蛋糕》《洋房里的女人》《送花的男孩》《第十个流浪儿》《笑队队员》等,大都停留于简单地反映人性善恶的层面上,极少涉及所处时代的背景和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