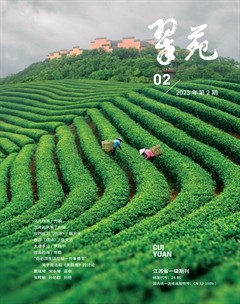春分已过,德国小城魏玛还沉浸在冬天的意象里。雪花扬落,渐渐隐没埃特斯山清晰的轮廓,留出蜿蜒的伊尔姆河尽头的锌白。红顶房屋不见缥缈的雾,白茫茫大地美好如斯。
魏玛大剧院门前那尊青铜雕像——歌德和席勒,傲然挺立冰雪之中,携手默默凝视远方,成功地搭建起帝国文明的高度,不动声色地将一个文化黄金时代呈现眼前。也许,当春风拂过大剧院的时候,整个小城都可以聆听到这里上演歌德、席勒的剧目:《浮士德》《威廉·退尔》。古典的叙事、宏大的乐团、深情的旋律,奏响一个伟大的时代。它自成的诗歌体裁,吟唱着特立独行的浪漫主义史诗……
这座风景优美、古色古香的城市,曾经被誉为十九世纪崛起的魏玛共和国。歌德和席勒于魏玛,如同空气一样无所不在。行走歌德广场、席勒大街,无不让人感到剑将出鞘的隐隐光芒,以及撼动世界的内在力量。
悠悠古意中,深情跨过歌德故居大门,仿佛进入一个太平盛世。宽敞的房屋,豪华的装饰,雅致的花园……透过书柜的藏书和矿物标本,依稀可见主人读书、写字的身影。壁上条幅、油画褐色边框光致而古旧,犹如一本本大辞典,浓缩一个时代的影像,徐徐打开。倚窗侧耳,便可听到嘚嘚的马蹄声,还有广场多情的圆舞曲。后院斜倚的草木,深掩春日的宁静,那些细细密密含苞的花蕾,淡雅而深远,像歌德隽永的文字……
风吹起窗纱一角,从寂静的一本本馆藏书前走过,侧目便看见那本熟悉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顿然欣喜莫名且悲不自胜。那一瞬间,一种无言的感动,一种文明厚重又轻盈质感萦绕心头。它曾经载着我的往事,陪伴走过经年。至今仍然隐约记得候浚吉的译本《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能给你带来幸福的,也能给你带来不幸。”“漠然于世吧,一颗微微激动的心。是这个摇动的大地上,痛苦的财富。”作者以书信方式的逐步深入,给我打开另一个世界,呼吸到不一样的新鲜空气。维特的内心独白将他的敏感、狂热、脆弱跃然纸上,读来为之愕然。他鄙视逆来顺受与循规蹈矩,崇尚自然、渴望自由、向往纯洁的爱情……这一切予以我最美的启蒙。然而,年少的我哪里知道,当时这本书初版正处德国文学启蒙运动“狂飙突进”时期,书中的文字竟然如救世主般挽救那么多压抑的个性、深陷黑暗的灵魂。主人公的爱情悲剧,不仅表现十八世纪中期德国青年对社会的愤懑,也露显鲜明的时代精神,因而被视为文学界最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
在岁月渐长的后天教化里,这份阅读的新奇被我小心翼翼地珍藏,成为串串记忆的宝物。今天来到这里,再次解读《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宽泛意义,以及深层、丰富的意境与内涵,逐渐明悟人的成长并非易事,从“天真”走向“成熟”的过程如此艰难。我以为,一个人的精神成长,以其笔下成长者的同构性与互文性,除了探究,更有文化之间的相互打量和融入,所以才如此亲切可感,生动可读。尤其作者亲身经历的体验与理解倾注文本之中,注定最为契合青年本质,并隐藏年轻人的视角,亦形成年轻人主题交流的逻辑支点。“人们总是在逃避命运的路上与命运撞个满怀。”从年少初读到现在深读,面临人生起伏,这种超越性的故事,告诉我如何理解自己曾急于成长又难忘少年的复杂情感。而真正动念深情的,是贯注现实和历史两种时空里交集的力量。如此,细细端详这本书,从而深入自己的成长世界,唤醒美善,启示向往,回望信念。
穿过一条街向北,即到达席勒故居。行走期间,不禁思如絮下。歌德与席勒这两位文学大师之间生死相依的旷世情缘,给后人留下多少动人的故事。他们初遇卡尔学堂,歌德被邀请为获得三枚银质奖章和医科结业证书的席勒颁奖。领奖时席勒亲吻歌德礼服表示感激,因不敢抬头,歌德的目光越过他的头顶而无交集。如此生动场景,至今想起还觉遗憾呢。而机缘却以“吾谁与归”之时迎来“引为同调”。1794年的某一天,席勒步行这条小路来回蹀躞,踟蹰不前的内心亦无定见。因为他写给歌德的那封热情洋溢的信,以及对其作品难以企及的理解,而受邀与之见面深谈呢。此时歌德如同魏玛公国的文化轴心,無疑也是吸引席勒前往的最好“万有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