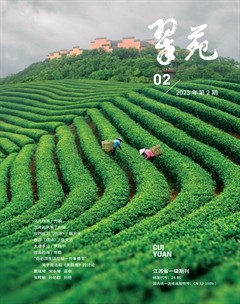蓑衣饼
张爱玲曾借她姑姑之口回忆家族旧事:“从前相府老太太看《儒林外史》,就看个吃。”她语气中不无调侃之意,我却以为这老太太不简单,因为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妇人没事喜欢翻翻经典小说,本身就很难得,这是其一;其二,《儒林外史》中的饮食描写确实出色,老太太爱看书中的饮馔文字,说明张家这位长辈还挺有审美眼光的。
我亦十分青睐《儒林外史》中的饮食文字,好像从14岁那年第一次读它起,就觉得书里的索粉八宝攒汤、鸭肉烧卖、鹅油白糖饺等等要比《水浒传》里的水煮牛肉、《三国演义》里的青梅酒讲究许多……不知相府老太太最爱《儒林》中的哪样美食,在我,几十年来最念念不忘的,要数马二先生游西湖时遇到的蓑衣饼了……
这一段的情节是这样的:正直、热情又有些迂腐的明代穷书生马二先生游玩西湖时,虽然游兴甚浓,但由于囊中羞涩到了用餐时间就颇感为难。怎么就为难了?主要是昂贵而美味的肴馔他无力购买,尽管看到“湖沿上接连着几个酒店,挂着透味的羊肉,柜台上盘子里盛着滚热的蹄子、海参、糟鸭、鲜鱼,锅里煮着馄饨,蒸笼上蒸着极大的馒头”,也只得掉头而去;便宜的面条无法吃饱;好容易碰到价廉而能混个肚圆的零食,那滋味又只能将就。正在意兴阑珊之际,马二先生恰恰邂逅了杭州名点蓑衣饼。
初见蓑衣饼我就暗暗吃了一惊。因为之前马二先生吃了有饺饼、芝麻糖、粽子、烧饼、黑枣等等十几种零食点心了,但他食用过后的反应不是“肚里不饱”,便是“不论好歹吃了一饱”,显见得这些点心皆不能令他称意。而这次在吴山品尝过蓑衣饼的反应就完全不同,书里说他到间壁一个茶室泡了一碗茶,看见有卖蓑衣饼的,叫打了12个钱的饼吃了,“略觉有些意思”。为何略觉有些意思?那自然是这饼滋味不俗,既垫饥又可口,同时价格还不贵,很对下层知识分子马二的脾胃吧。
马二先生迷恋八股文虽不可取,但我对他因帮助朋友而落到自己受穷的境遇,还是很同情的,捎带着对他称赏的蓑衣饼也充满了好感。这枚给予了一名寒士手炉般温暖的点心到底是怎样的?没见过。不过从名字上推想,应该是形似蓑衣,鹅黄饼皮层层纷披而下,艺术品一样精巧。究竟是何滋味?无缘领教,依然只能想象。既然它状若渔翁所披蓑衣,饼层自然制作得极薄极脆,咬一口定然又香又酥,托着这块饼的一刻,多大的烦心事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再多想几遍,这枚有着清雅名字的点心绝不仅仅是可口而已,它身上应该还有着林泉的气息,诗词的影子,慢慢品尝着它们的时候,你不由自主就记起一些名句来了,比如张志和的“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苏东坡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还有王士祯的“一蓑一笠一扁舟,一丈丝纶一寸钩。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等等……功课不那么紧张的时候我常在脑海里悄悄勾勒蓑衣饼的样子,对这枚家常点心的好奇、向往和思念就这样贯穿了我无比漫长的青春期。
不惑之年后才大致知道了这饼的模样,原因是那几年我读书的口味渐渐偏向于文史类书籍,也点点滴滴地积累了一些关于蓑衣饼的资料。原来这饼在明朝就有,是苏杭特产,以杭州吴山和苏州虎丘为佳。“城隍庙居吴山之中,其左右约里许,开设茶店甚多,茶则本山为最,饼则蓑衣著名。”这是清人范祖述在《杭俗遗风》里的记载,看来蓑衣饼在当地已有很高的知名度……滋味如何,一个叫汤传楹的明末才子在其《虎丘往还记》中有十分传神的记载:“予与尤子啖蓑衣饼二枚,啜清茗数瓯,酣适之味,有过于酒。”才子毕竟是才子,寥寥8個字就引得读者悠然神往了。
大概觉得此饼的滋味太过隽妙,清代大诗人兼美食家袁枚还特意去打听它的烹制方法,然后郑重其事将其收录于《随园食单》:“干面用冷水调,不可多揉,擀薄后卷拢;再擀薄了,用猪油、白糖铺匀,再卷拢擀成薄饼,用猪油煎黄。如要咸的,用葱椒盐亦可。”他记录得这般详尽,我一点不怀疑这位大名士哪天来了兴致,真会找出各种材料来做上一整天蓑衣饼。
这饼为何有这么雅的名字,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典故:其实它一开始的名字是叫酥油饼,后来文人们见其蓬松如农家蓑衣,谐音酥油,且蓑衣较之酥油更易入诗,于是给它改名,蓑衣饼的名字就这样流传至今。这件事并非哪个人杜撰出来的,它有清人丁立诚的一首诗为证,诗云:“吴山楼上江湖景,饮茶更食酥油饼。酥油音转为蓑衣,雅人高兴争品题。”
想来,吴敬梓先生也是偏爱蓑衣饼的,要不,他不会特地安排小说里的马二先生热烈赞美这饼——文士热爱此饼好像已成了一种惯例,记得著名的历史小说家、杭州人高阳在其代表作《胡雪岩》中,亦写道主人公胡雪岩在做钱庄小伙计时,曾与好友王有龄同上吴山喝菊花茶啖蓑衣饼的情形。
这几年听说现在杭州店铺又有了卖蓑衣饼的。闻听此消息甚是欢喜,因为杭州既有此物,苏州乃至我居住的城市不久大约也会看到它的倩影。周末的下午出门散步,一抬头就能与300多年前的杭城名点打个照面,可不正是中年人的乐事一桩吗?期待这芳馥的一天早些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