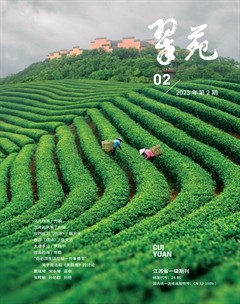戴瑶琴:周洁茹有三个标签,即代际、地域和类型,她一直跟踪“70后”成长,轻盈地在少年—青年—中年的时间沙盘,划出清晰的心灵轨迹。香港是小说集《小故事》与《美丽阁》的核心地域,或许这才是生活真相,对于必须在都市落地及扎根的每一个人而言,真正的痛苦都是难以言说、难以明说的,有时候叹息比哭诉更为伤感和悲情。我借用里尔克的诗句“你必须生活在每一件事情里”,作为探察周洁茹文学的阅读起点。
“美丽阁”的内涵及空间性
宋永琴:“阁”对于中年女性既是生存依赖的空间,也是仰望风景的窗;既是寄居其中不能摆脱的苑囿,又是灵魂寄放的美丽世界。周洁茹对“阁”这一空间很矛盾,人生要面对无数的困境与选择,“阁”已圈定了生活界域,同时,“美丽”的阁又发散着希望。小说刻画女性寻找自我、定位自我的过程,不管机缘如何,人总要“为自己挣一个明天”。也许每个人都在不断构建与寻找一座属于自己的“阁”。青春就是记忆深处的阁,“我”是旁观者也是亲历者,“美丽阁”整体意义是对逝去的驻足和远方的凝望。
戴瑶琴:“阁”的提出很亮眼,设计巧妙,它同时具有哲学性和美学性。小说里,“美丽阁”既是绝对空间,又是表征性空间,现实残酷与愿景美好的反差效果是“只能仰望,无法抵达”。
刘艳:是的,“阁”通常是飞鸟的游憩之地,而“美丽阁”在小说中其实存在于两处空间。在香港,它是一处公共屋邨(公屋),“太太群组”闲居此处。相较于久住“居屋”的阿美(《美丽阁》)和蜗居“劏房”的阿芳(《佐敦》),太太不曾体味“新移民”受制于身份或收入而无法入住公屋的煎熬。美容按摩、衣食物品、茶牌聚会粉饰香港逻辑自洽的“美丽”。师奶们偏安于现实一隅,如同无桅无舵的船只停泊于日复一日的琐事。在深圳,它是一间湘菜馆。老板娘阿丽从为他人美甲、带货的日子中出逃,朋友阿珍同样为了生计到深圳谋生。“美丽阁”不再是寄居幻景,只需如里尔克所言“生活在每一件事情里”。
张晖敏:在看到标题的“美丽”时,读者难免猜想作者要拆解出怎樣的不美丽,但通读之后,又会发觉这几个字的美好与空虚都恰如其分。文中的“美丽阁”由两个小区共享。地价飞涨,标识着各色身份的楼盘似乎只在这一点拥有着默契——永远不吝于在命名时使用大量溢美之词。芷兰金玉,亭台楼阁。“美丽”和“阁”放在一起,直白得冒着俗气。这也符合人们对香港的想象:高耸的昂贵鸽子笼,里面装着土与洋,贫与富,错位与融合。夸张名头对旁观者的意义更重大。阔太太和打工妹同样忙于和生活纠缠,地产商埋在广告里的小把戏并不能引起什么注意。只有当她们中的一个突然被按下了暂停键时,“美丽阁”才被还原为困窘和希望交织的真实生存空间,久违的荒谬与新奇也同步降临。
孙艳群:确实,只要现实的浑浊无法消解,美丽就只能存于阁中。小说中的阿珍、阿芳、珍妮花逐渐成为与单调生活同构的能指符号,冗余匮乏的生活细节将其追逐美丽的进阶路径剪断,无论是享受轻奢生活的太太组还是忙碌生存的普通妇女,女性都只能不断承受阶层固化带来的人生固化。于她们而言,美丽阁总凌驾于一层又一层的仰望之上,就像小说里说的“永远有更富的人”,那么也永远有更美的“美丽阁”。我觉得故事中的女性很像火烈鸟标本,落寞地站立在百鸟园之外。所有故事线的结尾其实都可以折回到太平山顶免费的观光缆车和收取海底隧道费的的士,在那里,428没有被赋予神秘隐喻,“我”积极回忆布鲁克林动物园的存在,其实是说服自己:“我”曾经有过纽约的朋友。
中产女性与中年女性
谌幸:周洁茹写作中一以贯之的“异乡感”,与《美丽阁》里中产生活、中年女性日常的题材可以说相得益彰。青春期过去后发现,真的漂泊、疏离在“人到中年”时发生。阶层浮动的脆弱和虚幻让中产者既感受不到彻底的快乐,也不再有冒险一搏的苦痛得失。也正是这种“异乡感”,让周洁茹的小说读起来始终有一种旁观者视角。她是敢于使用第一人称写作的作家,第一人称令其写作更加敏锐,而辅之以观察者的视角则拓宽视域。生活的苦涩不再局限于中产浮世绘或个人主义生活碎片,叙事对象有了更丰富且鲜明的层次,真实写出“富太”圈子的琐碎虚浮,也直面中下层女性互助中的艰难。同时,“异乡”或者“异乡人”作为存在主义文学的常用母题,本身就包含了基于中产生活内在裂变与循环的形而上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