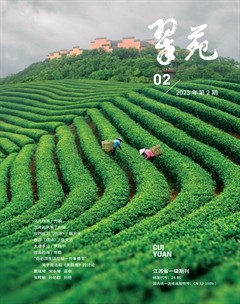文体是文学最为直观的表现,于文学文本而言,文体本身既是出发点,也是归宿,既有着独立的意义,也是意义的生成者与承载者。文体形式的可视性与稳定性还赋予了文学批评、文学学科以客观性、科学性。所以要学会从语言的物质本身来获取审美体验,从形式出发来理解内容,甚或把形式当成内容。针对辞赋这一特定体式,《隋唐五代辭赋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22)反复辨析律赋、文赋、俗赋等赋体体式特征,深入思考赋体体物特性对赋作类型特征、赋家题材意识乃至感物兴思理论的影响,全面考察赋家的赋作与赋论,彰显了隋唐五代辞赋的时代意义与赋史价值。渗透在全书的,不只对古今中外的文体学理论的广泛征引,还有对文学题材与文本形态、表现手法与文体特质、诗赋消长与文体演变、作家身份与创作心理、文史视角与文体理论等问题的系统思考,足见刘伟生教授在撰写这部断代文体史著作时的理论自觉。
体式文体与语体文体之论
就体式而言,赋介于诗、文之间,既多体多貌,又多源多变,《隋唐五代辞赋研究》从内容、手法、结构、语言、修辞、声韵等维度梳理了前人关于赋体文学特征的种种论说,指出只有将这种种维度合成一体,才能对赋体特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在概观各种分类方式之后,该书对赋体多元多变难于界定的体式特性还做了进一步的阐释,然后再落实到隋唐五代赋的赋体体式特性的解读上来。
王芑孙《读赋巵言》称:“诗莫盛于唐,赋亦莫盛于唐。总魏、晋、宋、齐、梁、周、陈、隋八朝之众轨,启宋、元、明三代之支流,踵武姬汉,蔚然翔跃,百体争开,昌其盈矣。”(王芑孙:《读赋巵言》,王冠辑,《赋话广聚》(第三册),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2006:311)隋唐五代辞赋的活力与价值,正在于承前启后、百体争开。为了再现隋唐五代辞赋“百体争开”的局面,该书围绕“隋唐五代不仅集散体大赋、骈体赋、诗体赋、骚体赋等传统赋体之大成,而且衍生出了律赋、文赋等新的赋作体式,并留存有杰出的俗赋篇章”的总体判断,展开对具体作家作品的阐释。
如论古文运动先驱赋,先从整体上评估古文运动对赋体革新的影响,说古文运动并未改变诗赋取士的制度,不可能从政治层面改变文体文风,再从逻辑上推论“古文理论必然影响及于赋家对赋体功用的认识,必然影响到赋家的创作态度,影响到赋体题材、艺术与体式”,然后从实践层面来具体分析在古文运动大背景下,赋体创作有哪些方面的革新,最后指出古文运动对赋体文学的影响是双面的,“既有建构也有解构”。这就是围绕文体形式而展开的系统研究。不仅如此,后面还有专节讨论《阿房宫赋》作为新文赋代表性作品的文体意义,可谓点面结合。关于律赋的研究,除了全面分析篇章结构、命题限韵、对仗用典、题材立意、审美风格等一般意义上的体式特征外,还结合徐寅作品研究了律赋体式中各部分的叙事功能。
如论“四杰”赋在文体体格上的开拓之功,提到了赋前多有骈文序言,赋作类诗类文、似骚似律,重点阐释了“四杰”在律赋的首创与七言诗体赋的定型上的贡献。指出在诗赋互渗过程中,“赋融于诗,从赋这边看是赋的解体,可从诗这边看,全速发展的歌行体最终消解五七言体赋而成为文坛描写壮阔景象、表达慷慨意绪的重要体式,也同样可以成就四杰在文体演变史上的地位”。还分析了“四杰”赋的语言修辞与整体风格,称其:“一面是精致流丽,一面却常用‘天下’‘九州’‘五湖’‘四海’‘万古’‘千年’等阔大悠长的时空词以及浩盛雄伟的风物,这与‘四杰’赋浩大文气的开拓也是互为关联的”,认为“浩大之气总得落实到浩大的语词与奔走的词调中来,只有这样才能锻造出整体宏大的气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