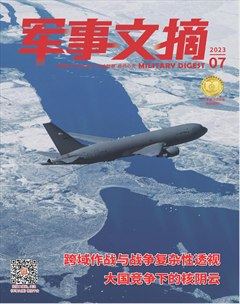美国综合威慑着眼于赢得大国竞争、重建印太和欧洲军事优势,秉持着“目的是威慑冲突,如果威慑失败,必须赢得战争”的国家安全理念。作为国防战略主导思想,综合威慑被奉为未来防务政策和军事战略的基石,明确了美军未来十年“打什么仗”。通过对该概念进行解析,并刻画其高端战争设计特征,有助于更好地研究美国下一步军事战略动向。
综合威慑内涵特征
2017年西方战略学界就开始了对综合威慑的研究。2021年4月,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在印太司令换届仪式上首次正式提出综合威慑,提出其需要可靠、灵活地将技术、作战概念以及各种能力编织成网,以建立分散、高度联通的军事力量。此外,还需要在所有潜在冲突领域寻求技术优势,推动跨域跨军种协同作战,开发新作战概念,提高整体威慑力。同年6月,国防部副部长科林·卡尔定义综合威慑为,将美国家力量的所有工具——核武器、常规武器、太空、网络和信息——整合在一起,并将它们应用到从直接冲突到混合非军事竞争的所有领域。随后,奥斯汀重申综合威慑是利用现有能力,建立新的能力,并以新的和网络化的方式部署它们,目的是使用工具箱中的每一个军事和非军事工具,并与盟友和伙伴同步。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先后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报告也提出了综合威慑战略,并将其视为美军事力量发展与提高的指导方针。
综合威慑基于传统威慑逻辑,即让潜在对手相信其敌对活动成本超过收益,内容主要包括跨领域、跨区域、跨冲突范围、跨部门以及跨盟友伙伴的一体化整合。其实施方式主要分为拒止威慑、弹性威慑以及直接和集体施加成本进行威慑,实际上仍是拒止型威慑和惩罚型威慑基于原则的灵活运用。综合威慑体现了拜登政府“低成本、非对称”应对大国竞争的战略思维,强调跨域使用威慑手段,让“任何想在一个领域取得优势的竞争对手明白我们也可以在许多其他领域做出回应”。
在以智能为特征的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推行综合威慑既是美国应对大国竞争与多重混合威胁的现实需要,也是受绝对安全逻辑下的霸权主义思想驱动,根本目的在于为中美在“决定性十年”从全面竞争走向全面对抗做好充分准备。

从综合威慑看美高端战争设计
战争设计是潜在对手之间没有硝烟的超前博弈,充斥着“技术迷雾”和“战略迷雾”。尽管综合威慑的战略规划、推进路径及落实策略等尚未公开,但其在近期国际冲突中的应用为我们研究美高端战争设计思想提供了鲜活的样板。
战略指导上凸显总体混合持久。综合威慑蕴含着“竞争-冲突-战争”连续对抗体的思想,现今大国战争胜利的意义在于为新一轮长期竞争夺取更大优势。核威慑背景下,理性的大国决策者通常不会轻易升级战争,而是更倾向于进行代理人式、混合的和持久消耗的军事竞争。一是全球、全域、全军种、全政府和全聯盟实力支撑。高端战争是大国间在各领域展开的全面对抗,关系着整个国家和民族以及联合行动盟友和伙伴的命运,需要整合整个国家和盟友的实力支撑。在战争前方,重点是武器装备、军事科技、人员素质的比拼,而后方则是经济、能源、金融乃至国民意志等战争潜力的较量。二是综合运用军事与非军事手段。综合威慑作为“混合战争”的“酵母”,需要统合各方面资源和力量,在政治、经济、外交、金融、科技等多个领域形成超出单纯军事范畴的多样化手段,寻求高端战争效能最大化。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提出,虽然并未公开宣战,但西方国家其实已对俄罗斯发动混合型全面战争。三是常态施压,持久耗竭。过去200多年,无论是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还是中美在朝鲜的大国战争,都是在高强度的军事冲突之后,陷入了战略相持。近年来大国间军事力量此消彼长,一些西方智库建议美国采取强化备战大国持久战的策略,以阻止中国将速决战作为军事战略的发展方向。因此,报告也汲取了“持久战”思想,提出变革国防生态系统以建立持久优势来巩固综合威慑和作战基础。
制胜机理上强调高新技术效用。综合威慑延续了“第三次抵消战略”核心思想,寻求对实力近等对手形成技术代差,以实施降维打击。奥斯汀提出,综合威慑作为 21 世纪的新愿景需要创新和投资,强调增加对人工智能、量子科学、自主技术、大数据和空间技术等高新技术领域的投入,以建立一支新的分散但高度联网的军事力量,并通过不断推动技术更新,促进美及其盟友和伙伴建立新的作战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