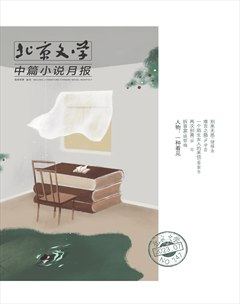1
2020年 4月 6日早上九点,我醒来拿起手机,看到班宇在凌晨三点十分给我发了几个短句,句与句之间显得呼吸艰难。
“老吴。”
“我今天刚知道,《逍遥游》的女主角,就是那个原型。”
“病逝了。”
“没什么事,有点儿睡不着,跟你说一句。”
我回复:“啊。我昨天很早睡。是做肾透析出了问题?谢谢告诉我。”
老班立刻就回了,像是根本没睡:“大概是晚期,然后引起各种并发症吧。”
我岔开话头说:“之前我记得你说她是亲戚的熟人?”
老班:“她爸爸是我姨的同学。昨天我姨来我家里,聊天时提到的。”
我:“就这几天的事?赶上疫情,那后事还得从简。”
老班:“每个小区门口都有个喇叭,每天循环播放疫情提醒,其中一句是‘红事缓办,白事减半’。我每天出门都想,你咋减、咋控制?后来发现是‘简办’,不是减半。”
我年前专程去过一趟沈阳,和老班一起转了两天,也去过他家喝茶,那是一个有着好几栋高楼的威风凛凛的小区,冬天里在单元楼门口挂着厚厚的夹棉门帘,一撩开门帘出来就看见高远夜空里冰粒般的几颗星子。他一说到小区门口,我立刻想起他在楼前那条长长的、疾风劲草的步道上躬身行走的样子。
我们最终不得不绕回来,直面死亡带来的撼动。老班的第二个短篇小说集正是以“逍遥游”为书名的。我说:“你后记里该记一笔。”他说:“我是想提一下。”
我最后说:“她留在文学里了。许玲玲安息。”
两年前的这个时候,刚认识不久,微信里我叫他班宇,他叫我“吴老师”。我们同样在谈论许玲玲,他正在修改《逍遥游》第四稿(其实就稍微动了几个字)。很快稿子定下来即将发在 2018年第四期的《收获》“青年作家专号”,不久又被定为头条。我给班宇发消息:“如果真有一个许玲玲的话,希望这是人间能够给她的慰藉。”
我所供职的《收获》双月刊每年都推出一期青年作家专号。1987年《收获》第五期、第六期“先锋文学专号”被视为这一传统的前身。余华、马原、苏童、格非、叶兆言、孙甘露、洪峰等人的作品通过“先锋文学专号”横空出世。余华曾这样回忆说:“1987年秋天,我收到第五期的《收获》,打开后看见自己的名字,还看见一些不熟悉的名字。《收获》每期都是名家聚集,这一期突然向读者展示一伙陌生的作者……这一期的《收获》后来被称为‘先锋文学专号’。”(余华:《1987年:〈收获〉第五期》)
时序转动,青年永恒。以距今最近的五年观,双雪涛、张悦然、孙频、旧海棠、常小琥等新一代作家从“青年作家专号”起步,不仅中短篇,还包括周嘉宁的《密林中》、笛安的《南方有令秧》等长篇小说。
2018年的“青年作家专号”赶上一个特殊的机遇:格非主持的清华大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与《收获》联手,邀请部分作者参加于清华园举办的青年作家工作坊。
这年7月,我和我责编的三位作者班宇、郭爽、董夏青青在工作坊碰面了。有件事颇可一记:军中作家董夏青青提议我们彼此破除客套,以“老”相称,她率先慨然喊我“老吴”。从此,1983年出生的我、1984年出生的郭爽、1986年出生的班宇和 1987年出生的董夏青青成了老吴、老郭(有时简称“爽”)、老班和老董。
工作坊中,每个人的作品都要拿出来“过堂”。《逍遥游》获得的大部分是美誉。格非评述为“震撼,迷人,回答了人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还有没有欲望的问题”。他还注意到小说中一些看似微末的细节特别准确,“父亲给许玲玲从沈阳去秦皇岛旅游的钱,不多不少,五百元,是一个贫困的父亲刚好拿得出来的、刚好够这样一趟短途旅行的用度,并且因其少但又不是极少而令人心酸”。班宇在“答辩”时说:“这个小说一部分来自亲友的真实讲述,写的过程中受尽折磨,不忍心写。最后写成这个样子,我想表达的是生命状态急迫关头的一种短暂逃逸,同時也想写这么一种人物的状态——你在与人间若即若离的时候,不仅得到了单纯直接的爱,自身也还在努力反馈着爱。”
2018年下半年,老班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短时间内广为人知。他原本在豆瓣、微博上就具有超高人气,再叠加上了期刊、媒体、评论的影响力,又因其来自东北沈阳,某种文化、时代与社会的奇观效应隐现其后。2018年 10月,他的首部短篇小说集《冬泳》问世即畅销,因一波影视演员的转发而加速“出圈”。2018年 12月,第三届《收获》文学排行榜颁奖典礼上,我和老班再次见面时,他已被九位评委票选为短篇小说组榜首。授奖辞曰:“作者就像是从巨大的崩溃中幸存折返的人,他掌握着满手的细节,慢慢陈列一些,又藏起更多。一段翻滚着尘世悲欢的穷游,既看山河风景,也探幽微人心。”
在他即将上台领奖的那一霎,我举起相机给他拍了张照片。“这一刻是成名在即,下一刻就已大红。”我把照片发过去时说。
2019年是比 2018年还要红的一年。老班以前写的和正在写的小说被全国多家文学期刊以最快的速度发表。他还成为时尚媒体和诸多文学奖项争相邀请的对象。有一次,我看《智族GQ》的报道才知道,某一夜他就在上海展览中心,在我所在的编辑部走路五分钟可达的地方,但这五分钟恐怕已经是名利场宇宙的外缘。
2019年 9月的一个早晨,我和老班讨论完一个新短篇,忽然随口(但其实也是蓄谋已久)问道:“一个小说反复谈,和你每天面临的那些新鲜的、复杂的事相比,可能是最单一的事情?”
老班:“我觉得……生活没有本质变化,我还在单位跟老吴谈稿子。”
我心里没有设置标准答案,但老班的这个回答堪称优秀。我由此知道他依然是“许玲玲”们的画像者,是替命运暗河中那些嘶哑无声的溺水者放声歌唱的人。
他正在写的那个新短篇就是《夜莺湖》,三个月后发表于 2020年第一期《收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平评价这是“班宇写得最好的一篇小说”—— “在当代文学中较为罕见地把握住了这种回望关系,将消逝的世界赎回。 ”(《寓言与忧郁——论作为悲剧的班宇小说》)
2
来沈阳之前,老班用心良苦反复叮咛要穿厚实一些,零下十几度,不能穿那种薄得像纸似的棉衣。我只好专门添置了一件长到脚踝的新羽绒衣。及至在酒店门口见到他也穿得像个包子,连唯一露出来的脸也冻得白里透红,我失望地说:“怎么你也这么不扛冻?”老班怪叫一声道:“东北人也是人啊!”
在我看来,“东北人也是人”和“东北发生的小说也是小说”一样,是个很明显但又不得不去重新辨析的事实。这几年的话题中,似乎倾向于把东北单独地从一个完整的时代和幅员中割裂出来,抓住它的普遍特征推到极致,成为奇观。可是,走在工人村的阡陌街道上,走在职工宿舍院中,走在劳动公园里,除了喷涌的暖气白烟、矗立在院外的浴室和人们在结冰的湖面上速滑这些场景稍显陌生外,大部分场景与我童年成长的南方城市并无二致。
我同意老班的话:东北既不是我写的那样,也不是你认为的那样,它具体啥样,你就自己来看一看。
老班走在大路上,向左一挥手,向右一指点。工人村周边曾经有富于文艺气息的乐器行、书店、花店,现门面还在,人去楼空,只有一家炖肉馆还在营业,声名远扬,顾客盈门。
“铁西区北面都是工厂,南面都是家属区,我们就在南边。大家都骑自行车上班,早上黑压压一片,都在红绿灯这儿等着。现在你看到的这个是拖拉机厂的家属(宿舍)区,斜对面是印刷厂的家屬区,我们要去的是变压器厂家属区。我爸妈都是变压器厂的。住在这儿特别有安全感,从来没丢过小孩。”
我跟在后面,咔咔拍着照片。我问他“变压器厂最特别的地方”,他回答“最特别的地方是大,亚洲最大,一个厂子有几十万人,相当于一个县城的人口”。我说,“那你爸遇到你妈真不容易”,他说,“他们是双方父母介绍认识的。”后勤部门和工会的二代联姻。
在到达变压器厂家属区之前,还经过了热力厂宿舍楼、工人村浴池、东北制药厂宿舍、自行车配件厂宿舍,以及一座煤山的原址——往日一入秋就开始囤煤,高得吓人,班宇和他的同学们经常爬到上面去玩,现在这里是一片空地。自行车配件厂应该已经不存在了,而变压器厂卖给了新疆来的一个商人,现在只有千余人上班。
班宇带我一拐弯走进院子,抬头看那个封着的钴蓝色阳台窗,后面就是他二十六岁之前生活的家。在2012年,这套五十二平方米的房子卖了三十万元人民币,而现在“可能二十五万还卖不到”。家属区虽然身居市区,但不对应热门的好小学,又旧,卖不上价。
在宿舍楼还没有参与房产买卖的年代,家属区的直观含义就是:父母的父母、父母的同事,自己的同学,学校的老师,全部都是邻居。补课就是从1号楼下来去 4号楼。离开七八年了,老班还经常会一个人回来转转,来维护或者勾兑记忆的原浆。
一个同学的妈妈,是个大胖子,在粮油店负责卖油炸糕,是一种糯米里边带着红豆馅的食物,小孩最馋这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