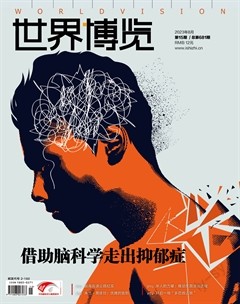无锡这个地方盛产大画家,最早可以追溯到晋朝的顾恺之。离我们比较近的则是现当代画家徐悲鸿、吴冠中。在这个“时间轴”的中段,还有一位就是“元四家”之一的倪瓒,他也是笔者最喜欢的中国画家。
几年前我去无锡旅行,专门去拜谒了倪瓒的墓,那天下雨,感觉正是我印象中湿漉漉的江南。墓园旁边是一家小小的纪念馆,可惜的是,那里没有收藏任何原作,展出的大概是日本二玄社出的高精度复制品。的确,倪瓒留下的画并不算多且过于珍贵,只有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等一些大馆珍藏了有限的几幅。
“懂”中国画的人太多了,每个人看画自有其角度,笔者从“感受”出发,谈谈我喜欢的倪瓒。
感受“文人画”
倪瓒的画属于“文人画”体系,是文人、士大夫们抒发情感、表达人生观的一种“业余”艺术,与专职画家的“院体画”在绘画风格和价值取向方面,都有很大不同。总的来说,文人画比较素雅简洁,多用水墨少用色彩,技法相对简单,笔法与墨法都脱胎于书法。
“文人画”起源于唐代的王维,他是山水田园派诗人,因此山水画也走诗意的路数,这是“文人画”在艺术观上的基础;五代的董源、巨然,则为后世“文人画”的发展提供了技法方面的积累;到北宋时期,苏轼、文同、米芾等人,将“士人画”的理论和实践系统化,很多文人画的主题慢慢确定下来,“文人画”也逐渐成为中国绘画艺术的“主干”;到了元朝,由于汉族文人处于被整体打压的状态,因此,他们的境遇与“文人画”表达的隐逸、遁世思想空前一致,再加上多年实践积累,“文人画”在元朝达到了巅峰,出现了元四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这样的高山;明清两代,“文人画”保持着很高水平的发展,尤其是江南一带,出了很多大画家,包括我们都熟悉的明代沈周、唐寅、文徵明等,清代的“四僧”“四王”“扬州八怪”等大画家绝大多数都是文人画家。
不得不说,“文人画”的立意是好的,艺术趣味也是高级的。纯从艺术来看,中国画的笔墨形式,很接近西方的抽象艺术,单纯地欣赏笔法、墨法、皴法,欣赏线条灵动、布局巧思、墨分五色。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画是“早熟”的。但是在“文人画”的发展过程中,抒发情感、表达人生观的“初心”走了样。
大多数情境之下,“文人画”并不走心,画家想“表达”的价值观自己并没有从骨子里认同,也就不可能画出“感觉”来。而且在“诗、书、画、印”一体的评判体系中,“画”也成了“诗”和“书法”的附庸。因此,“文人们”并不会真正花心思在画本身上,“文人画”在创新上没有动力,最终蜕变为痴迷于“笔法”“墨法”的“笔墨”游戏,走向了纯形式——八股、模式化,模式化的“文人画”,最终表现心性大多只能靠题材。这也是大多“文人画”不太让人感动的原因。因此,“画如其人”的文人画家更是凤毛麟角,而倪瓒则是其中非常彻底地画出了真我的一位。他的厉害之处在于,虽然“文人画”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模式化,但他的世界观在画中一眼就能“看”到、“感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