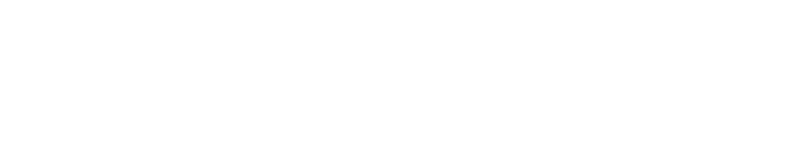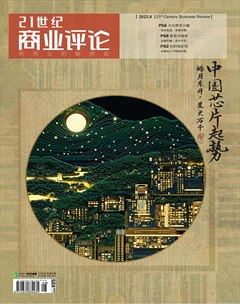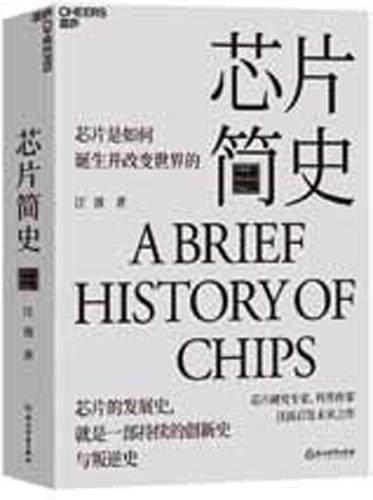
即便许多年过去,张忠谋仍将在博士入学资格考试时的失利,当作人生最大的幸运。
他不是失败了一次,而是失败了两次。
1954年2月,张忠谋第一次在麻省理工学院机械系博士入学资格考试中失利,教授多给了他一次机会,允许他第二年再尝试一次。整整一年,他都在用功复习,成绩揭晓后,张忠谋站在榜前,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
按照麻省理工学院的规定,两次通不过,即永远失去申请资格。
此时,张忠谋已经成家,父母在美国经营着一家小店维持生计,他又是独子。十几年的寒窗苦读却被突然叫停,张忠谋深受打击。
张忠谋不敢相信,自己竟然会在学业上受挫,他成绩一直优异。
抗战期间,他进入重庆南开中学,每天吃榨菜和粗糙发黄的米饭,学习桐城派古文;胜利后,他到上海读商学院,后再次到中国香港,申请到哈佛大学就读,之后因为要读理工科,又转学到了隔壁的麻省理工学院。
在麻省理工学院,张忠谋投入了5年的青春年华。如今,一切都结束了,查尔斯河边的机械博士梦碎了。
其实,这次失利不只是他个人最大的幸运,也是中国台湾科技产业的幸运,甚至是苹果、超威半导体(AMD)、高通和联发科等世界一流科技公司的幸运。
阴差阳错,张忠谋进入了陌生的半导体行业。
新竹领命
1955年,即张忠谋博士资格考试失利的那一年,他四处找工作,拿到了福特(Ford)汽车、希凡尼亚(Sylvania)半导体等4家公司的聘书。
他本已拿定主意去福特公司,那里的岗位不仅跟他的机械专业对口,且工作稳定,这对刚刚结婚、需要赡养父母的独子张忠谋来说,很有吸引力。
福特公司给出的月薪是479美元,比希凡尼亚半导体低了1美元。
张忠谋拨通了福特公司人事经理的电话,希望福特提高一下起薪。
“我们不讲价,如果接受就来,不接受就请便。”面试时还谈笑风生的人事主管正色说道。
年轻气盛的张忠谋感到被羞辱。他开始反向思考,是去干一份四平八稳的工作,还是去半导体领域冒险?
他最后的决定是:去希凡尼亞半导体公司!就这样,区区1美元之差改变了一切,随后的人生轨迹也完全转向。
在希凡尼亚半导体公司,张忠谋先工作了3年,后又在德州仪器公司 (Texes Instruments)做了25年,位至副总裁。
其后,他结束了在美国36年的生活,来到中国台北郊外的一片“处女地”——新竹工业园。
1985年,张忠谋接任中国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院长。上任第一天,前一任院长方贤齐拿着一张清单来找他,上面列出了该院的优先待办事项。
来新竹之前,时为中国台湾经济事务负责人的李国鼎,数次邀请他,张忠谋一直没有下定决心,直到李国鼎提出,张忠谋可用他在德州仪器公司的经验,来帮助台湾地区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工业经济增长。
“这是一个无法拒绝的邀请,就像电影《教父》里的情景。”张忠谋动心了。
方贤齐的清单里,有一项建立一家晶圆制造厂的规划。他叮嘱张忠谋,李国鼎对此事非常重视,可能过几天就要来当面商谈。
李国鼎被誉为“中国台湾科技教父”,制定了台湾地区的科技发展策略,还担任着应用技术发展小组召集人一职。
果然,张忠谋很快就接到了李国鼎的电话,李国鼎邀请他参加会议讨论。
“我们计划大力推动半导体技术的发展。你有丰富的半导体业务管理经验,我们希望你创办一家新的半导体晶圆制造厂。”李国鼎希望张忠谋回去后想一想,拿出一份可行的计划书,期限是一个星期。
回到工业技术研究院的办公室,张忠谋开始思考。
在半导体行业,当时,台湾地区能够拿得出手的,几乎没有什么——既没有优秀的芯片设计公司,也没有广阔的市场。
在德州仪器公司工作多年的张忠谋清楚,半导体是全球性产业,只有做到世界一流,才可能有立足之地。
当时美国实力雄厚,欧洲紧随其后,日本异军突起,而中国台湾基础薄弱,没有任何积累,一家新成立的半导体公司,要想开拓出一片天地,何其困难!
唯一可能的一条路就是,扬长避短。
台湾地区有什么长处呢?只有一些中低端的制造业,当时最大的制造企业是台塑。
那么,制造业会是半导体产业的未来吗?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地区的工厂替代日本,开始为欧美企业加工成衣和玩具,从中收取微薄的加工费。
在人们心目中,制造业一直是一个低端行业。人们用“微笑曲线”描绘制造业的地位——高附加值部分集中在“嘴角”,分别是研发和市场;低附加值部分则在向下弯曲的部分,那里是制造业。
制造立业
现在,张忠谋来到中国台湾新竹,他又要面临一个选择:
是像德州仪器公司那样开办一家传统半导体公司,还是去做别人不敢做的事?
张忠谋选择后者,他将目光聚焦到芯片制造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