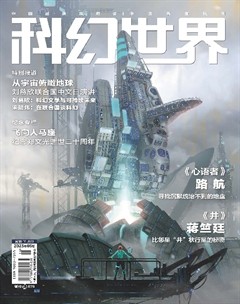主持人说:
在以往的科幻影视作品中,类似《终结者》《机械公敌》等人工智能题材的作品,一直在探讨自主思考的AI给人类世界带来的变化。近两个月以来,现实最接近科幻想象的地方,便是ChatGPT横空出世、快速迭代,其进化程度几乎呈指数级增长,惊人的数据处理能力和通过自我学习不断提升的能力,远超人类想象。人工智能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势不可挡地深入人类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在某些领域甚至开始代替人类工作。人类怎样依托人工智能找准自己的定位,成了新的社会问题。
脑洞时间:
AI时代的人类有哪些新职业?
上
我是最熟悉这座城市的人。绝对是!
我熟悉它,就像熟悉自己的身体。每一棵树,每一块LED屏,每一条烂水沟,每一座摩天大楼,每一次日落时阳光在林荫大道投下的阴影,每一个春天开始时野猫在街角的躁动情绪,我都烂熟于心。
如果你觉得这样讲太过绝对,那么,我至少也是最熟悉这座城市的人之一——八万分之一。剩下的七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是我的同事。我们是这座城市的眼睛和耳朵——人工智能训练师。这份工作并不光鲜,好在它至少是稳定的。这个年头,有什么比稳定更加重要呢?
我站在狭仄的出租屋里,脏兮兮的镜面里是一个看起来并不春风得意的中年人,深重的眼袋和倒退的发际线在昏暗光线下倒不那么碍眼。
“或许你得快点出门了,宝贝。”娜娜的声音从厨房传来。
“好。”
“给你做了麦片粥,有點烫哦。如果等它凉下来,你就该迟到了,带去公司喝吧。”
我抬头看了一眼时钟,数字停在6:40,路上还需要挤在沙丁鱼罐头一般的地铁车厢里整整一个半小时。上个月,同事阿梁迟到十分钟被辞退,现在只能从出租房搬出来,一家五口蜗居在蚁棚里。想到这里,我一刻都不敢怠慢,穿好鞋,从娜娜手里接过粥,快步走出门去。
“等等,再急也不能忘了……”娜娜在背后小声说道。
我愣住,无奈地笑笑,转过身去,在娜娜的嘴唇上落下一个吻。她与五年前相识时一样活泼动人,在这个轻吻里,淘气地向后跷起一只脚,像偶像剧女主角一样,仿佛置身在青葱校园,而不是通风极差的廉租房。
等我气喘吁吁跨入公司的感应门时,屏幕显示8:20,冗余的十分钟刚好够我喝完已经冰凉的燕麦粥。然后,一天的工作开始了。
8:30,电脑显示出由无人机和巡街机器人拍摄的街景照片。每一个无法被“城市大脑”识别的物体都会被打上红色方框,我的工作就是为这些方框里的物体标上名字、归类,标注其特征。
“城市大脑”——这个中枢计算机系统是管理城市的秩序之神,也是最脆弱幼稚的婴儿。“有多少智能,背后就有多少人工。”这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一句老话了。我们的这座城市每天生产的数据量已经增长到1600ZB,其中80%以上是非结构化数据,这些数据经过清洗、标注,变成结构化数据后,才能被“城市大脑”理解和学习。
举个简单的例子,该如何教人工智能从零到一认识一只猫?我们得先有猫的图片,上面标注着“猫”这个字,由机器学习千百张猫咪图片的特征,这时候再给机器任意一张猫的图片,它才能认出来。人工智能训练师就是用自己的人工,训练“城市大脑”的智能,用每一天在屏幕上的千百次点击,换取人工智能一点一点认识世界的全部面貌。
说来讽刺,小时候我的梦想是工程师,大学考上了电子工程专业,就在我以为毕业将要在互联网公司一展身手时,人工智能革命袭来。以人工智能技术驱动,拥有语言识别、图像生成、代码撰写能力的“城市大脑”替代了大量劳动密集型的初级技术岗。我还没毕业,就失业了。
就业市场变得前所未有的严峻,曾经炙手可热的专业文凭,成了废纸一张。是啊,写代码,谁能写得过人工智能呢?好在我的大学排名全国前三,凭着这张文凭,我从几百个应聘者中脱颖而出,成了一名人工智能训练师。
四墙雪白的平层办公室里,挤着八十个机位,每台主机发出的微小声音交织成一片蜂群似的嗡鸣。这样的机房,这栋楼里还有一百多间,这样的机楼,这座城市里还有一百多座。每工作两个小时,我们会获得一次去卫生间的机会,每四个小时可以休息三十分钟,可以去贩售机里买食物吃,也可以静静地在吸烟室里抽一根烟。
“AI可不会累,‘城市大脑’从来不需要吃饭抽烟上厕所。”每当我心里抱怨工作条件,脑子里就浮现出这句入职时总管说的话。我是学电子工程的,而搭载了最先进人工智能技术的自然语言处理系统只需要十秒就能写出我十天工作量的代码。当我一次次将屏幕跳出的红框标注成“狗/金毛/正在过马路/无危害性/无须处理”,或者“塑料袋/一次性用品/飘在树梢头/需要巡街机器人清理/非紧急”,那抢了我饭碗的“城市大脑”只会越来越聪明,直至聪明到认识世间绝大多数物品,甚至再也不需要我们这群人工智能训练师在屏幕前日复一日地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