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巨鹿路675号的外墙上,挂着“上海市作家协会”“收获”“上海文学”“萌芽”几块招牌。其中,《上海文学》作为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创刊最早的综合性文艺刊物,今年迎来了70周年华诞。
在《上海文学》的编辑部里,有一把做工考究的西式扶手靠背椅,迄今已走过近百年历史。自创刊以来,巴金、靳以、魏金枝、钟望阳、茹志鹃、李子云、周介人等前辈都在这把椅子上坐过,率领《上海文学》走过当代文学史的每个阶段,见证了新中国文学变迁的风风雨雨。
《文艺月报》时代
《上海文学》的历史,始于1953年1月创刊的《文艺月报》。
1952年,华东文联和上海文联在巨鹿路675号合署办公。下半年,巴金、黄源、唐弢、王西彦、石灵、刘雪苇、靳以、赖少其、魏金枝九人组成编委会,开始筹备机关文艺刊物《文艺月报》。巴金任主编,但不负责具体工作,黄源、刘雪苇、唐弢任副主编。九位编委都是20世纪30年代成名的青年作家,多数编过同人刊物。他们当年都是“鲁迅身边的青年作家”,“文艺月报”四字就是经刘雪苇提议从鲁迅书法中集字而来。
《文艺月报》自创刊后就有强烈的同人色彩。“编者的话”表示,要以反映人民的斗争生活和推动各地的文艺工作为方针,同时认为,除一些政策性文章外,其它文章所言并不都是结论,提倡让不同的意见都有充分发表的机会,互相商榷,互相探究,以达到正确的结论。对这些多少有些“异端”的理念,《文艺月报》采取“迂回”策略,在表现形式上力求委婉。
初期的《文艺月报》生气勃勃,陆续刊发了巴金的《坚强战士》、师陀的《前进曲》、卞之琳的《采菱》等老作家作品,也推出了王安友的《追肥》、陈登科的《离乡》、高晓声的《解约》、昌耀的《诗两首》等新人新作。
在圈内看来,《文艺月报》对外严,对内宽;对新严,对老宽。在一次编辑部会议上,有编辑提出某位老作家的作品描写了大量生活琐事,显示不出主题思想,一位编委举出别林斯基的话加以反驳:“只有描写日常生活的才是天才,追求轰轰烈烈斗争场面的是庸才。”
《文艺月报》自创刊伊始,就存在所谓的“胡风派”与“周扬派”一说。主编巴金和第一副主编黄源都鲜少介入编辑事务,编委中的真正主事者是副主编刘雪苇和唐弢,其中实际主持工作的刘雪苇得到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彭柏山支持,唐弢则受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夏衍支持。早在30年代,夏衍和周扬就名列“四条汉子”之中,而刘雪苇、彭柏山则一直得到鲁迅和胡风的帮助,与胡风素有私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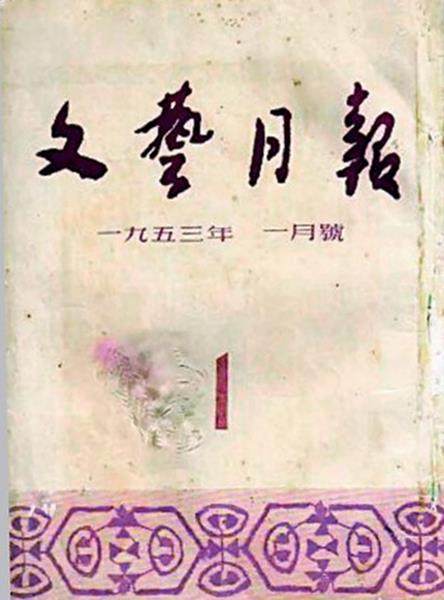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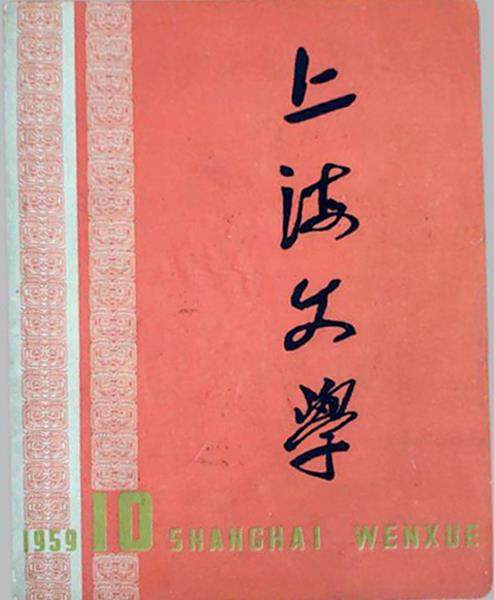
不久,刘雪苇不再兼任《文艺月报》副主编,唐弢成为实际负责人。1953年12月,上海作协第七次主席团会议决定改组《文艺月报》编委会,由巴金、唐弢、靳以、魏金枝、王若望、王元化、叶以群、孔罗荪八人组成新的编委会,刘雪苇不再担任编委。
刘雪苇性格强势,敢于任事;而唐弢则缺少革命资历,性格圆融。1955年刘雪苇被牵涉进“胡风案”中,被列为该案的第二号人物,蒙冤24年,直到1980年才获平反。
经过这些变化,《文艺月报》的同人色彩逐渐淡化。1954年底,《文艺月报》展开自我批判,检讨报纸不恰当地去追求艺术的“完美”,而忽视了生活里天天在茁壮成长的、来自群众的新生力量。
1957年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写出了长篇论文《论“文学是人学”》。 当时苏联《文学原理》认为:“人的描写是艺术家反映整体现实所使用的工具。”钱谷融则提出,文学当然能够而且也必须反映现实,但反对把反映现实当作文学直接的、首要的任务,尤其反对把描写人仅仅当作是反映现实的一种工具、一种手段,否则其结果就是,“那被当作反映现实的工具的人,却真正成了一把毫无灵性的工具,丝毫也引不起人的兴趣了”。这篇文章成为大力提倡“双百”方针期间影响最大的文学评论文章之一。
《文艺月报》理论组组长傅艾以曾回忆,当时编辑部认为这是一篇很有理论价值但有可能招来非议的文章。唐弢一贯谨慎,他估计到可能产生的后果,在文章发表之前让编委们传阅,又派人去与作者沟通,并将文章打印50份,分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有关领导以及一些著名文艺理论家和教授审阅。各方反馈不一,但无一人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最终,文章发表在1957年5月的《文艺月报》上。
此时恰逢“反右”运动前夕。很快,《文汇报》率先发表批评文章,更广泛的批评随之而来,还专门集结出版了《<论“文学是人学”>批判集》(第一集)。《文艺月报》观望了两个月之后,在8月号上发表了吴调公的《论“文学”与人道主义》,在9月号发表罗竹风的《人道主义可以说明一切吗?》。两篇文章基本没有超出学术争鸣范围,在版面处理上也与其他刊物不同。此后,《文艺月报》没有再发表批判《论“文学是人学”》的来稿。
傅艾以曾说,唐弢文风酷似鲁迅,为人处世亦都处处以鲁迅为楷模。鲁迅好友沈尹默多次讲过:“鲁迅深于世故,妙于应付,也同他所擅长的古文词一样,为当时士大夫之流所望尘莫及。”钱谷融幸免于难,没被打成“右派”,除诸多因素之外,与唐弢在发文前采取了一些措施、特别是广泛征求了各方面意见也有一定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