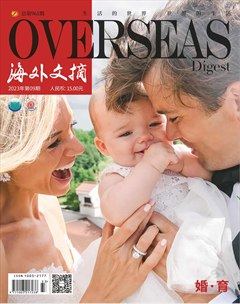2019年冬日里的一天,40岁的巴黎人玛丽躺在超声波检查台上,望着漆黑一片的屏幕说:“我已经不抱希望了。我知道,我没有卵母细胞了。”为了怀孕,她和丈夫努力了五年。期间经历了两次流产。最近一次的体外受精也没有成功。为了刺激卵巢,玛丽接受了大量注射,但一颗卵子也没能取出。她说:“我还能回忆起我脑中‘想要孩子’的开关突然关上的那一刻。有些事情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我发现没有孩子也可以很快乐,孩子不是幸福的必要条件。意识到这一点,一切都变得简单了。”
| 技术仍不能解决不孕不育问题 |
在法国,每四对想要孩子的夫妻中就有一对无法生育。这一比例还在上升。在大龄夫妻群体中,不孕不育的问题尤为显著。人们天真地认为,技术手段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然而,法国辅助生殖医疗中心的新生儿出生率仅有20%。对于25%至30%的夫妻来说,无论做了多少努力,最终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辅助生殖医疗中心的患者了解这些风险吗?“一般来说是了解的,但这确实会给患者造成很大的情绪负担。每个人都会对自己说‘一定会成功’。”辅助生殖慈善团体邦普的创始人韦尔金妮说。玛丽说:“我不想知道失败的概率,否则我就没有勇气继续了。”韦尔金妮发现,不孕不育患者往往以为药物能治愈一切。只要做一次试管,就能拥有宝宝。然而事实上,部分疾病或基因异常——比如卵母细胞缺陷或子宫内膜异位症——都会让这个过程变得复杂,甚至彻底葬送为人父母的可能性。
2016年的一项研究显示,1/4的伴侣在第一次试管失败后就会放弃。“在不孕不育的治疗之路上,患者的生理与心理都承受着巨大压力,有的人受不了就放弃了。”韦尔金妮说。邦普致力于为患者提供身心陪伴。他们会组织线上讨论,聊一聊“没有孩子的生活”。参与者来自法国各地,大多都在独自忍受没有孩子的痛苦。在亲朋好友中,他们是“特殊的存在”,不被理解。

桑德里娜是邦普的志愿者,负责协助组织线上讨论会。她自己也已经对“当妈妈”这件事不再抱有希望。谈起这群“不被看见的人”时,桑德里娜说:“他们的年龄介于30至50岁之间,有些人尝试了一年后就放弃了,有些人则努力了十几年。大部分患者都有另一半。但许多人表示,夫妻关系快要维持不下去了。也有部分患者是独身女性,她们的婚姻已经破裂。”我们问桑德里娜:“你是怎么接受自己无法生育的现实的?”她回答道:“我还记得以前的我是怎么样的,有哪些事情会让我激动不已。现在,我过着很普通的生活。我不再觉得生活亏欠了我什么,我也不再想要补偿。”
要走到桑德里娜的这一步,需要很长时间。一开始,患者满脑子都会想着如何能拥有一个孩子。他们会按照计划同房,不停地抽血做检查,定时接受注射,摄入激素类药物。他们的日常生活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在希望与失望之间来回起伏。更别提经历胎停或是发现自身有所缺陷后,心理遭受的创伤。他们的生理、心理、工作、日常生活、自尊心、夫妻关系,无一不受到影响。“我已经分不清,我是在和我的丈夫生孩子,还是在和我的医生生孩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