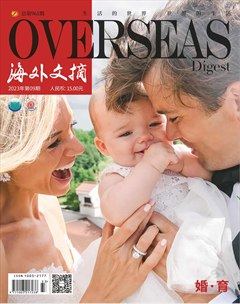| 漫漫求子路 |
在湖区举办的单身女性派对上,我的朋友们组织了一场夫妻游戏。对于未婚女性来说,这个游戏考验了你对未来配偶的了解程度。她们提前给我的伴侣伊恩作了测试,在派对上让我回答同样的问题。最初的问题很寻常:你俩第一次接吻是在哪儿?你俩谁的衣品更好?但突然间冒出的一个问题给了微醺的我当头一棒:“你最害怕什么?”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如实回答,我深知自己内心最恐惧的是什么,但我也清楚这个答案是何等煞风景。无论如何,我开口了:“无法生育。”言毕,我周围短暂地沉寂下来。在播放伊恩的测试录像来活跃气氛之前,朋友给我斟满了酒。当时我36岁。
在经历了多次受孕失败后,那场夫妻游戏的场景反复出现在我脑海中。不孕不育带给我的感受复杂且莫名,耻辱感就是其中之一。我为自己毫不遮掩想要个孩子的渴望而羞耻——我曾夸下海口要生四个孩子,如今我为无法兑现当初的诺言而尴尬。
我相信天道酬勤。我从小就立志成为一名记者,14岁时我便给当地电台工作人员写信,告诉他们为什么我的同龄人对电台节目毫无兴趣。我大胆的行为引起了兰开夏郡广播电台的注意,他们给了我每周一次进行电台直播的机会。长大后,我特意选择了一个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学习的专业(德语),以保证自己可以全身心投入到采编学生新闻的工作中。
我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大学毕业后我在《卫报》工作,30岁时在柏林担任驻外记者。飞往柏林前,我与朋友在酒吧相聚,我试着抱了抱朋友刚出生的宝宝。我素来喜欢孩子,但拥有自己的孩子对那时的我而言遥不可及。我有太多想做的事情。
等我终于找到合适的伴侣成家后,我早已过了最适合生育的年龄。我周围许多朋友都生了二胎。我38岁时开始尝试试管婴儿手术,那段时间我恰好有一位同事待产,她那如篮球般的孕肚时时在提醒我缺乏生育能力的事实。社交媒体似乎到处有人打着“赞美母爱”的标签,炫耀孕妇二维超声扫描图和婴儿用品套装。我将自己内心的酸涩隐藏,假装为他们感到高兴。
我开始强烈地敌视那些老牛吃嫩草才有了孩子的二婚中老年男星。我拒绝看他们演出的作品。我对自己不得不顺应朋友接送孩子而调整见面时间十分反感。在我日常的记者工作中,一旦涉及儿童忽视相关案件,我遭受的精神打击是前所未有的:我不能生孩子,凭什么这些渣滓能有孩子?
我养成了怪异的习惯,譬如坚持收看第五频道关于英国最大家庭雷德福的系列纪录片《22娃数一数》。雷德福一家就生活在我的故乡莫克姆。2020年4月,45岁的女主人生下了她第22个孩子;而在同一时期,由于新冠疫情,我的试管婴儿手术不得不推迟。那时我和伊恩格外敏感,任何与孩子有关的信息对我们来说都是折磨。看电视剧时,我会因为男女主角准备要个孩子而痛哭流涕;我扔掉原本看得津津有味的女强人主题杂志专栏,只因为在倒数第二段读到她生了对双胞胎。
当我开始更为坦率地接受试管婴儿技术时,那些儿女众多的人所发表的一切言论都会点燃我的怒火。如果他们跟我说“没有孩子反而轻松”,我会对他们虚伪的怜悯不屑一顾;如果他们试图说“有预感你这次胚胎移植会成功”来让我高兴,我反倒会想揍他们一拳。试管婴儿失败率高是公认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