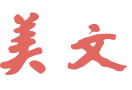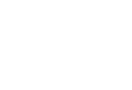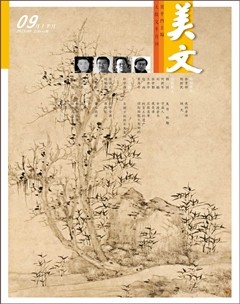“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
——《孙子·行军篇》
一
孙子这句话,一度引发了我的中年恐慌。“半渡而击”,是军事思想的精华,也是庸常人生的实景。
当你跨越童年懵懂,实现青春冲刺后,你抵达一个指向不明的拐角,像阿尔戈英雄们迎来一次次惊险——曲径、三岔口、十字路,或者山坡、低谷,甚而悬崖、深渊。它极具发散性,然万源归宗,最终都将趋于缓慢收缩的瓶口。恭喜你!你已步入中年。
“中年”是一个复杂的词语。可以是盛年,强壮而雄心不已,可以“仗剑入紫微”,也可以“妖艳浮华辈”。但你处于半渡状态,如果有人不按规矩出牌,偷袭你,封锁你,你该怎么办?这里的“人”,可以是一个具体的竞争对手,更多的可能是你自己——你的精力,你的身体,你的家庭,抽象且无形。它们在半路上剪径,设置了障碍,导致你倍受羁绊,倍感烦心、琐碎、无奈。元人张之翰在《木兰花慢》一词中,说的甚好:“自中年以去,觉岁月、疾如流。渐鬓影萧萧,人情草草,世事悠悠。”“还自叹、中年多病,不堪离别。”辛弃疾在《满江红·送李正之提刑入蜀》中,不可避免地抒发了他个人的中年恨。我几乎同时想到了一个朝代的“中衰”,继而让“中兴”有了粉墨登场的意义。
少年时,摔跟头似乎必不可少,跌扑所引发的疼痛是表层的,而由成长带来骨骼、肌肉的阵痛,则深入肌理。现在好了,你跨过了成长期,疼痛不仅依然存在,还往往更胜于从前,可谓痛在骨髓。但凡经历了中年之殇、之疼、之痒、之徘徊、之挣扎、之看破后,写下的字词句,都会少一些风月,多一点劫后余生式的苍凉。以至于现在,当我提笔写下这些文字时,我一直处于自我“舒风止痛”和归纳总结的状态,忍不住用回忆、反思和倒叙的方式重温那段初入瓶口的困惑。
二
早些年,关注落叶归根的问题。写过一个短篇小说,题为《失落的牙齿》,讲述大学生蒋长山,年轻时不甘窝在农村,遂进城打拼落户城市,享受着城市优渥的生活条件。随着年龄老去,生命日薄西山,他“良心发现”,重新意识到落叶归根的重要性。当又一颗牙齿在喷嚏声中轰然陨落时,他忍不住想要实现一种“生命的回归”。他一边回忆着童年换牙时的乡俗,将下面的牙齿藏在屋瓦间,上面的牙齿埋到树根旁。等他把最后一颗牙颤巍巍放入屋瓦间时,他终于松了口气,觉得一辈子都没有长大,一辈子都井然有序地保留着故乡的习俗。故乡情结在城市、在他身上开出了一朵奇葩。就在他酝酿着重返故乡的计划时,一夜风狂雨骤,他的梦也紧扣外界,风雨大作,将他的牙齿“连根拔起”,卷入洪流,拍打着老家的家门(此处,颇有奇幻色彩)。梦醒后,他赶紧寻找牙齿,结果一颗也找寻不着,这才意识到梦是一次天启,从而开始了一个七十多岁老人孤独而又热烈的返乡之旅、寻亲之路。然而,故乡已物是人非,他无法重回童年故土,百感交集下,他只得强作豁达,以为“吾心安处是故乡”,“双脚踏入那片土地,无论它多么陌生,多么喧嚣,都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亲切,是他可以感知的,而这种感觉,这片土地上的其他人未必能体会到”。
在城里的这些年,我先后失去好几颗牙齿。我童年营养不良,头发稀疏、发黄、早白,牙齿也不够齐整,缝隙大,易摇晃,笑的时候习惯性抿嘴,显得格外腼腆。本家有个堂叔,自学中医,说我肾虚。
《杂病源流犀烛》载:“齿者,肾之标,骨之本也。”意思是说,齿与骨同出一源,且硬于骨头。说人嘴硬者,实际上说的是他牙齿硬。前年,我去甘南拉卜楞寺,晚上围着篝火看藏族女孩载歌载舞。我夜幕下什么也看不清,只看到她们的一口整齐的牙齿,像极了饱满的白玉米,羡慕得想咬牙切齿。当地人对于牙齿,并没有我们平原上的人这么重视,但他们却拥有了扎尕那雪山般洁净和坚硬的皓齒。离开甘南的路上,那些女孩的笑容令我五味杂陈。在我这里,我越是想要护它们周全,它们越显得异乎寻常的脆弱。人们对“岁月催人老”的真切认知,不是从额头开始,就是从牙齿开始。从一颗牙齿的分崩离析,我们渐渐对岁月有了“惹不起”的慨叹、“躲不起”的抓狂。
套用海明威的名言。岁月是一座冰山,它漂浮在海面上的永远只是20%,80%的问题你看不见,摸不着,无色无形无味,就那样不知不觉地,我们被撞了一下腰。然后一声惨叫,荡气回肠。
三
人到中年,是一个适合调侃的阶段。你可以自诩油腻大叔,这样就有理由精心准备自己的日常标配:枸杞、红枣、桂圆,外加一只保温杯;也可以梳着油光锃亮的日渐单薄的发型,微笑时裸露额头上的江河湖海,走路时摇晃无处遁形的酒囊饭袋,搬运东西时聊作呻吟语。失眠像一头黑豹,于夜阑人静时趁虚而入。
据说,黑豹的性器具有倒刺。这倒刺是什么样的?是只有一根,还是像猫的舌头密密麻麻?最近,家里养了两只猫,其中一只非常喜欢舔我的手、额头。舔我额头时,既酥又痒还疼,像我正在经受的失眠之感。
有人认为失眠是时间惹的祸,就像月亮是爱情的酵母菌。然而,失眠本身与时间并无绝对联系,是灵与肉之间的暧昧。这倒让我意外地想起三岛由纪夫的一部小说名《潮骚》。失眠如潮水,始终骚动不安地拍打着船上的人,他一袭黑衣,正体验着川端康成式的“生存原本就是一种徒劳”。失眠者,是忧郁的,如川氏,也是刚烈的,如三岛。
在失眠面前,我们无一例外地成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青年时期也极有可能罹患失眠症。有趣的是,青春可以挥霍,人们大可以享受那种失眠。躺在床上,在白月光的烘托下,可以给自己设定无限可能的未来。还有一波人,他们相约派对,在夜店浮世绘的刺激下一醉方休。
中年人的失眠,犹如古寺古钟敲打着孤舟孤客孤旅,真实而猛烈。一种病态。病着,且是一种常态。在这种常态下,我们普遍做着一件诡异的事情,像普鲁斯特在《追寻逝去的时光(第5卷):女囚》中所说的“把时间、年代和事物都按照它们的顺序排成圈,围绕置放在自己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