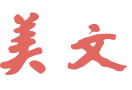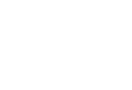一
我很清楚,我是一块石头,一块巨石。在深山之中,在群山之上,在风中。有一个人经常孤坐在我身上,看着每日里的太阳东升西降,风云变幻,万物运行。他在苦思冥想这世界怎么了,为什么。天宽地阔,却一片荒芜,这总不是办法。太阳一天一个从东边出来,又一天一个去西边降下,这总不是办法。与女娲是兄妹,却又成夫妻,这总不是办法。
我知道了,他叫伏羲,屁股热热的坐得我发烫。他结绳记事,结绳成网,把陶埙吹成了天籁,把琴瑟弹拨出共鸣。他自言自语,从有到无,从无到有,一可以生二,二可以生三,三可以生万物。万物往复,生生不息,循环无限。
他終于开窍,一画开天。他的世界,终于成为日月星辰和大海。
这是一个思想者的劳动!这是一个孤独者的收获!
后世的人们从此记住了《易经》,人们一头大汗,手脚并用,忙于研究,仔细揣摩世界浓缩成的那64张面孔,却并没有人关注伏羲曾经坐过的那块石头。
我就是那块石头,一块巨石,一块顽石,伏羲的屁股印还印在我的头上。
二
公元前535年,鲁国巷党。公元前518年,周都洛邑。公元前498年,沛。又过几年,鹿邑。
这些时间和地点,与两个人有关。他们一个叫老子,一个叫孔子。他们之间的见面,后世给出一种很壮观的说法,叫火星撞地球。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是一棵树,尽管一会儿是槐树,一会儿是柏树,一会儿是楸树,一会儿是杨树。我知道的是,他们每次见面,我都站在他们一边,他们那些高深莫测的交谈,我都听得一清二楚。
他们一个在北,一个在南。一个年长一些,一个年轻一些。一个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一个重礼,一个说礼只是工具。一个尚仁,一个认为仁的概念太宽泛太模糊。那个年纪长一点的说,人啊,再聪明也要少非议,懂得再多也不要动辄教训别人,真正有钱人应该让人看起来像个穷光蛋一样才行,真正有修养的人应该让人看起来像个傻瓜蛋一样才行。总之,要想在社会上混出点模样,要知敬畏,毋以有己。
像两个空手道高手,他们云山雾罩不着边际地谈了很多,他们之间的对话虽然不能完全听明白,但确实也挺有意思。但我的意思是,两个人的见面早已经被界定为一个国家的重大历史事件,他们的对话内容早已经被确认为一个国家思想史的原点。从那时起,一个东方大国的高端思想和先进文化便开始江海横流。可他们身边的那棵树呢,根本没有出处,查不到记载。
三
公元64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汉明帝刘庄做梦,梦见一位神人,全身金色,项上更是金光闪耀,在自己的宫殿前不停在绕飞。大臣傅毅为王解梦:“此所谓得道者,能飞于虚空,神通广大,这叫佛。”
汉明帝以为此事吉,对得上自己永平这个年号。经过大半年的筹备,第二年蔡愔博士及弟子秦景等十人便受帝王之托远征西域求法。使团到达大月氏国,抄得佛经42章,然后寻得一匹白马,驮着这些经卷外加一部分佛像,于公元67年返回。汉明帝亲迎城外,并专门建寺予以承接。是谓白马寺。
我说这些的意思是,我就是那匹白马,一路的辛苦至今历历在目。我还知道迦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高僧跟我们一路同行,留下许多偈语。由东往西,由西往东,我们打开了一条通道。直至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在研究那42章经文,却没有一人去研究那匹白马。尽管我对那些经文,亲身称过它们的重量,早已倒背如流,对其内涵甚至比那些研究者吃得更透。
我一直在白马寺外面转来转去,不肯离开。在别人看来,我的使命早已经完成,后面历史的进程无论怎么宏阔,怎么沉重,怎么逍遥,都已经与我无关。可我自己并不这么认为。我以为我完全有资格也可以成为一名高僧,或其他足以让人记得住名字的人物,但这作为一匹马的想法,一定会被认为很荒唐。
有人说了,不是已经建起一座白马寺了吗,你应该知足。
是。可我认为,白马寺终究是一座寺,而并非一匹白马。
四
我不清楚我为什么会变成女人,但单于认为我适合嫁给那个被俘获的东方人。我相信单于的做法,绝非是考虑到我的爱情,而只不过是想收住那个俘虏的心。我跟从来就不曾相识的一个异族男子,一待就是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