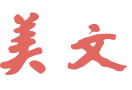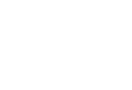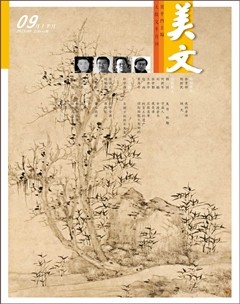夏夜走过中原
2022年暑假我在中原老家呆了11天。这十一天,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中原大地似乎变成了热带亚热带地区,从早上七八点开始,就是38、39度的高温,人根本不能在室外多呆。白天,整个村子空空荡荡的,被高温熏蒸烘烤着,直到下午五点钟之后,大家才能走出家门,稍微做些事情。晚上气温会下降一点,是出门游历的好时机。但是,因为持续高温,村里干旱得厉害,夜行动物极少见,反复搜索,也仅仅是见到了一只拟步甲,一只中华蟾蜍,几只壁虎,以及很多只蟋蟀。
除了村子,我也在田野里晃悠,整个颍河冲积平原,正是玉米大豆的生长旺季,举目所及,沃野千里,良田万顷,却寂然无声,全没有了若干年前螽斯齐鸣、蚂蚱飞溅的盛况,《寂静的春天》里描写的场面,已经成为事实。除草剂和农药的大量使用,确实杀死了大量杂草,灭掉了许多农作物害虫,这种情况对农作物增产是好事,但是对生物多样性却是巨大的戕害。孰优孰劣,真的不是一下子可以说得清楚。
为了看到一些东西,我只有夜上颍河大堤。颍河大堤上种满了树,树下有杂草,也许会有东西看。然而,这些树却都是单一的经济林,忽而一大片全是槐树,忽而一大片全是杨树,忽而一大片又全是枫树,一棵棵整整齐齐,高矮一致,树冠大小统一,株距远近一致,好在并不单调乏味!
不过,无论如何,应该还是有东西可以看的。
晚上九点多,田野里弥漫着玉米叶子的青气,偶尔的艾蒿味,风里有微微的凉意。夜晚的田野,到处都是虫鸣唧唧,这些声音,绝大多数来自蟋蟀。我在玉米地边静静蹲了一会儿,只听到微弱的噼噼啪啪声此起彼伏。认真看看,玉米根部的土块里,有无数的蟋蟀进进出出,它们跳起,飞一段,弹到玉米叶上,又落下来,整个夜晚乐此不疲。
《豳风·七月》里说:“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当时的周历以夏历十一月为正月,推算下来,如今的农历七月正是诗中的九月,这两天,我也在自己房间里看到了蟋蟀,《诗经》所言“九月在户”看起来确实有此事。现在是农历的七月初,大暑节气已经过了半个月,马上就要立秋,天气炎热潮湿,食物充足——正是蟋蟀们生命中的黄金时节,它们要竭尽所能地鸣唱,求偶,交配,产卵,以便在肃杀的秋冬来临之前,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就这片地里,就在这个时刻,就有成千上万只蟋蟀乘着夜色忙碌自己的婚姻大事。几乎所有的螽斯和蝗虫都已经从这片田野上消失,但蟋蟀却每年都能大量孵化出来,在田野中大啖农作物,并做了盛夏之夜田野音乐会的主角,这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但现在肯定不是蟋蟀最旺盛的时候——记得小时候,外公曾经在田野的灯光下用扫把扫了半口袋的蟋蟀,一大早送到我们家里,现在应该没有这样的盛况了。
现在田里绝大多数是秋作物玉米,整个田野里充斥的也是蟋蟀此起彼伏的唧唧声。这声音单听起来纤弱凄惶,但它们组合起来,却是铺天盖地的声音洪流。唧唧唧唧,唧唧唧唧,高高低低,长长短短,尽管声音高低、频率并不一致,但它们却全方位地、立体地、一刻不停地占据了这盛夏的原野之夜。夜晚穿行在田野里,就要分开这闪闪发光的声音之河,溯流而上。
颍河河堤上有一条大路,堤下,颍河水清浅羞涩,宛如小溪,在宽阔的河床里无声地流着,再没有了1975年的暴脾气。谁能想到,1975年,就是这样一条浅浅的水流,居然突然暴涨,在半夜决堤,掀起滔天巨浪,在黑暗中吞噬掉无数生命?
白天,河堤上浓荫匝地,蝉声悠长,人车不断,纳凉者也不少;夜稍微深一点,这里就空无一人,只有河水慢慢流着。河堤上,车灯所到之处,只见大树在头顶环合交接,仿佛庄严的拱顶,你将由此走进一个黑暗广阔神秘的世界。只有到了这种时候,你才又意识到,这里是大自然的地盘,只是容许人类白天在这里稍作盘桓,晚上,它又收回了统治权——于是,夜晚的气味變得荒蛮浓烈,而你的脚步和说话的声音立刻小心翼翼起来。
天空暗蓝,一轮清晰秀美的上弦月挂在河上,北斗七星斜斜地躺着。因为有月亮,银河并不是很清晰。车灯照射下的路面空空荡荡,只有偶尔一只蝙蝠在灯光里一掠而过。白天这里有无数上下翻飞的黑卷尾,根据它们嘶哑难听的叫声,吾乡人叫它“吃杯茶”,现在它们不知道哪棵树上睡着了。
一只小动物踽踽地爬了出来,大概是想横穿路面。我赶紧踩了刹车。它动作并不灵敏,体型也比一般的老鼠大。刺猬!我看到了它拱起来的背,背上尖尖的白刺,以及它富有辨识度的尖鼻子。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野外的刺猬。没想到颍河大堤上还有这等野物。这小小野物的存在,证明着颍河地界还没有被人类完全收复改造,还有一些在人类秩序之外的野性。
我走过去,它停住了脚步,但并没有如我想象的那样蜷缩成一个球,而是伸长鼻子默默等待着。第一次面对这野物,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想起乡人说野外的刺猬极臭,我于是用脚尖碰了一下它,以为它一定会缩起来,哪知道这轻轻一触,就让它极为敏捷地掉转头,哧溜一下就滑进了草丛,没给我留下一点细细观察的时间。咳!后悔死我了!
第二个晚上,我仍旧来巡路,希望又能偶遇那只刺猬。这一次,没有看到刺猬,却意外地看到一只黄鼬躺在路边,它没有外伤,只有眼珠子外凸,显然是横过马路上遭了意外。这只黄鼬体形矫健,皮毛土黄,尾巴大概有身体的1/3长,即使挂了,也能让人想见它当日生机勃勃的样子。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黄鼬,即乡人口中富有神秘色彩的“黄大仙”。不知道这名“黄大仙”为什么命中有此一劫,悲哉!
匆匆两三次夜游,勉强算是看到两种野物,我意犹未尽。我总想在熟悉的地方发掘出它另外的东西来,比如,在秩序外看到异端,在熟稔里遭遇陌生,在遍地顺服中发现野性,在规规矩矩中邂逅旁逸斜出——这些是多么美好的愿望!
当然,这些愿望也在逐步实现:去年冬天,在这片田地边的大杨树上,我几次看到一只普通鵟镇守在自己的领地上,一群又一群的小云雀在冬小麦田里飞起又落下,河里漂浮着一队队鲜艳的赤麻鸭;今年暑假,在一片早早收割完的玉米地里,我又看到了十几只灰头麦鸡,许慎文化公园柏树林里,则有一地的黑尾蜡嘴雀和金翅雀……在熟悉的故乡里细细搜索,发现它让人惊喜的另一面,就像跟一位故人聊天——在旧有的交情基础上,你又发现故人又有新思想与你产生共鸣,你们不仅仅有过去共同的回忆,还更有此刻的心领神会——这是何等的喜悦!
被封控的夜晚
2022年8月17日,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