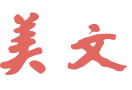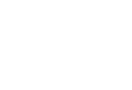罗先生家喂了一只黑白相间的花猫,经常悄无声息地穿过猫洞,从这间房游走至那间房。偶尔亦可见它蜷缩在罗先生膝间打瞌睡。其时,躺椅上的罗先生必定在看书。罗婶则轻手轻脚,将一杯茶放在茶几上。罗先生居然欠欠身,说,谢谢。
倒脱靴十号是栋老公馆,红砖房子。离巷尾近,离巷口远。坐南朝北,但大门开得有些古怪,偏西北,斜斜地对着院子,估计与风水有关。大门上方横嵌一块花岗石,上刻“心远草堂”四个字,当取陶潜诗句“心远地自偏”之意吧,遒劲而清秀。“文革”初期“破四旧”,我大哥一时兴起,拿把榔头搭张梯子打算砸烂它,结果只砸出来几处白印子加几粒火星子。
大哥本来蛮懒,做事从不想出汗,加之仅仅打算出点风头而已,便不了了之。结果直到三十多年后倒脱靴十号被拆毁,“心远草堂”这块石刻才不知所终。
说此类建筑为公馆,其实并不确切。据说,公馆的本意应是“仕宦寓所或公家馆舍”,即旧时公家替在本地任职的高官建造,并非私人所有。但后来被引申为有钱人家在城里盖的高级私宅,也就约定俗成了。小时候,长沙人亦将住公馆叫作住“洋房子”,似乎更合适一些,因为公馆房子多为西式,中式少见。
我家是二十世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搬进来的。房东姓罗,一位半路出家的医生,长相儒雅斯文,对人客客气气,邻里都称他罗先生。我家跟罗先生租下了朝北最大的一间,二十平方米左右,开三张床,晚上再用门板搭临时铺,能勉强挤下一家七口,父母和五个子女。不久,祖父与姑妈(我父亲的姐姐)也搬进来了,租了与我们房间相通的南房。因姑父原是一位国民党军官,年轻时风流倜傥,与姑妈的婚姻系双方父母撮合,两人谈不上什么真情实感,新婚未及两年,竟带了个越南舞女去了台湾,给姑妈留下一个刚满三个月的儿子,再杳无音讯。姑妈从此独身,带着儿子一直随祖父居住。
房东罗先生也有好几个小孩,其中一个与我一般大小。后来都在小古道巷小学读书,不过他甲班,我乙班。小学毕业后几十年再不曾见过面,但都还记得对方。早几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又恢复了联系,后来彼此还加了微信,在朋友圈里间或有些呼应。因为这幢公馆原本是他家的私产,我曾特意在微信里给他留言,想听他讲讲关于心远草堂最初的故事,后来因何缘由卖掉了,等等。罗同学的回信令人不无感慨。
他告诉我,他们祖上的湘阴老屋,就叫“心远草堂”。曾藏有不少古籍、字画及碑帖什么的,可惜毁于一场山火。抗战胜利后,祖父在长沙盖了这栋公馆,仍沿用此名,聊作纪念。至于后来卖掉,乃因二十世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响应政府号召,支援国家建设买公债,一时拿不出现金的无奈之举。
房子卖给谁早不记得了。
这事我倒比他清楚,房子卖给了一个做南货生意的资本家,号称长沙市的南货大王,叫李福荫。即心远草堂的第二任房东。
此外,罗先生所以半路出家学医,乃从祖父之命。因大女儿出生不久即死于缺醫少药的抗战时期,故祖父痛定思痛,嘱其务必弃商从医。所拜名医姚光仲就住在倒脱靴四号,即十号的斜对门。“心远草堂”在建的同时,罗先生亦购得黄兴南路一栋临街房屋,为行医开诊所做准备。这美好的愿望后来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化为泡影。
对倒脱靴十号最初的印象,似乎已介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因为其时我不过三四岁。大约是院子里正下着纷纷扬扬的大雪,很冷。堂屋搁了一盆炭火,时不时毕剥一声,窜出来几簇火星。房东罗先生穿一件蓝布棉袍,手捧一卷线装书在堂房里踱步,嘴里还念念有词。那时应该正是他拜师学医时期,在诵读什么汤头歌诀之类吧。
我跟罗同学则站在阶基上朝院子里屙尿,比谁屙得远。洁白厚软、尚无一只脚印的雪地上,顿时被两道小小的抛物线浇铸得一片金黄。还听见结了冰的玉兰花树叶发出悄悄的脆裂声。罗同学那个疯子姑姑(叫巧姑子)则在幽闭她的后院小屋里蓦然发出一声清籁:
“巧姑子要呷茶哒咧……”
巧姑子是罗先生唯一的妹妹。听大人说过,她是在大学里念书时,因失恋致疯的。
罗同学小时候脑壳很大,是个显而易见的特征。一般人都认为大脑壳愚蠢,罗同学用自己的大脑壳不声不响地推翻了这种成见。很可惜,如今要具体地回忆起小学里跟他有关的某件事,很难。因为他家早已搬离倒脱靴,在小古道巷小学我们也不同班,交往更少。倒是一些没有什么意义的片段却浮现在脑际。
比如说有一次,为了准备一组以做好人好事为题目的宣传栏,学校组织甲乙两班几个会画画的,包括我跟罗同学,集中在甲班的教室里画画。记得我画的是一位少先队员帮助掏粪工人推粪车。罗同学画的什么我当然忘了。忽然窗户外面飘进来一股似有若无的槐花的香味。我说,好香!罗同学连忙把铅笔搁在纸上,大脑壳转了一圈,很响亮地缩了一下鼻子,说,闻不出。
罗同学身上显然有他父亲的遗传因素。读书聪明得很。而且他们姊妹兄弟,个个会读书,个个性格好。从不跟人吵架,谦和而且沉静。从罗同学姐姐到罗同学本人再到他弟弟,臂上全都是三根杠杠,包揽了连续三届的少先队大队长,堪称小古道巷小学空前绝后的奇迹。
街坊叫罗同学的母亲作罗婶,个子清瘦,有点弱不禁风的样子。穿着朴素但显得精致,阴丹士林蓝布妇女装的右襟,插着一方洁白的手帕,干干净净的。说话声音细小温和,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罗先生卖掉倒脱靴十号后,即搬进了黄兴南路他们家另外那处临街的房子。但其时已不具备开诊所的条件,门面只好租给了一家茶叶店。路人但凡经过,本应闻见药香,却变成闻到茶叶的香气了,也好。多少年过去,只要偶尔想起罗婶,我竟会同时联想到茶叶隐约的清香。
小学时候,我在乙班画画画得最好,罗同学在甲班画画画得最好。我喜欢画动物,他喜欢画人物,各有千秋。但到了五年级罗同学当了大队长,我却还是个小队长,当然有几分沮丧。班主任段老师便偷偷安慰我,不要当官,就是长大了也不要当官,管好自己就是。未料段老师一语成谶。我迄今当过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一回“官”,仍然是少先队的小队长。一根杠杠。
可惜即便一辈子从未做过官,也未见得就管好了自己。
不过我有篇作文《我的理想》曾得了全校作文比赛第一名,还是令我神气了好多天。那时候,“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长大了要当一个像时传祥伯伯一样的掏粪工人”。时传祥当时是北京市的一个掏粪工,曾经红极一时的劳模,受到过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