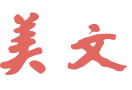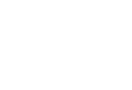初中考试完后,我便上山开始挖药草挣学费。暑假快结束时,有传言我考上了中专。那时中专很吃香,因为这意味着跳出农门,毕业便可以直接吃国家饭了。这个消息传到我的耳里的那一天,我正好顶着烈日与父亲在田里薅秧锄草。不知什么时候起,在山上露水杂草中曾无数次跑来跑去的我,身上碰到秧苗就过敏,一下田腿上便痒的不行。我父亲还认为我偷懒,忍不住开口就骂:“你是吃这碗泥巴饭的,多痒几次就习惯了。你还以为你有公家命呀。”我忍着泪,蹲在秧田中扯草。这时,田埂上有一个邻村人路过,看到了我,就高兴地对我父亲说:“大哥啊,恭喜你啊,你儿子考上中专了!”父亲不信,再三确认。邻村人走后,父亲回过头,看我的目光瞬间便变得温柔了起来。他对我说:“原来你果然不是吃这碗泥巴饭的。既然你身上痒,那就回去吧,我来干就行了。”
回到家,我看到母亲眼里闪烁着泪光般的喜悦。一家人,坐在灯下,大家都不说话,静默许久。母亲说:“伢啊,终于苦穿头了啊,好啊好啊!”母亲说话时,抚摸着我的头。我便低下头,看到父亲与失去上学机会的姐姐,都用特别高兴而又复杂的眼神看着我。
但几天后,真正的消息传来,却敲碎了全家的希望。我们班不仅没有一个考上中专,而且连高中都上不了了——因为我们自己的乡镇没有高中,其他乡镇的高中,原则上只招本镇的学生,这导致我们乡镇的孩子上高中的名额很少,而且录取分数还很高。仿佛在寒冷的冬天浇了一盆凉水,我一下子掉进了冰窖。我们全家都掉进了冰窖。一家人又重新坐在家里,全部保持了沉默。深夜里不时有母亲的叹息声传来。而我,同样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想不开。推开窗,村庄一片漆黑,窗外弯月如刀,仿佛在我心头一点点割肉。
母亲披衣坐起来,问我怎么了。我强忍着泪,说没什么。母亲说:“伢啊,人的命,天注定。不要急,明年再好些来。”母亲坐着床头,我突然觉得愧疚溢出了胸膛。在那个夜里,我第一次对人生产生了绝望的感觉,甚至想到了死。
为了能上高中,父母开始托人漫无边际地找关系,最后几经周折,只能去百里之外的一个镇上职高。由于离家远,为节约车钱,我一般是一个月回去一次。除了每个月初背一袋米来,还得带上更多的咸菜。
“既来之,则安之。”班主任说。班主任姓彭,是一个好老头,教我们的化学与无机土壤等。那时,我开始真正静下来,读书、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像往日那样,我在新的学校里还是被大家推选为班长。与初中的快乐学习不同,那是我见过的失败情绪最厉害最严重最泛滥的班级,也是对人生抱着失望感最沉最重最绝望的学校。虽然同学之间温暖而团结,但几乎没有人想到以后可以跳出农门。那时,身边好多同学开始谈恋爱,开始自暴自弃。而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漫无目的开始写作,每天待在一个角落里,不停地写。作为班长,我偶尔在晚上自习时,组织大家讨论人生。但無论大家争得如何面红耳赤,最终谁也无法说服谁。我甚至觉得每天的生活都了无生趣。我们班主任——那个胖乎乎的中年人,脸上一直带笑——却常常鼓励我们要积极向上,要在广阔的农村田野里干出一番不凡的事业。他相信事业与成功的存在,正如我们相信失败迟早会来。我确实又经历了一次失败。因为我唱歌不错,一个来选苗子的老师推荐我去参加县楚剧团的招生考试。我当时信心满怀,骑着一辆借来的自行车在寒风中出发,经过一个多小时到了县城,但进去唱了几分钟,人家便把我淘汰了。回来的路上,下起了雪,我觉得那些雪都下在了我的心里。
心情如此,学习如此,生活也是艰难。最难忘的事是偷菜。偷菜一般以班级宿舍为单位,大家轮流去镇上菜农的菜地里偷一些白菜、萝卜,再偷偷用电炉子放点盐一煮,滴上几滴油,便是佳肴了。轮到我去偷菜了,我却不敢去。我们班的张同学说:“你胆子小,我陪你去吧。”借着朦胧的月色,我猫着腰跟在他屁股后,进了农民伯伯的菜地。刚摘了几根黄瓜,有两个人打着手电,从公路那边的岸上向菜地里跑来。同学张跑的快,一下越过了河岸,“扑嗵”一声跳进了河流。而吓得大脑一片空白的我跟不上同学张的速度,只有选择往菜地那边比较深的高粱与玉米地中跑,竟然一脚踩空,跌进了种菜农民挖的土厕里。我在农民的脚步声中瑟瑟发抖。等两个人的确走远了,我才从粪坑中爬出来,向河边跑去。张同学在河里等我。我哭着说:“打死我再也不会偷菜了,从明天起,我也不吃你们偷的菜了。”回到宿舍,在同学们的哈哈大笑声中,同学张说:“以后不能再让他去偷了,我们也不要去了,这迟早要出事的。”大家想想也是,便集体研究决定,每个人轮流从家里背一些能存放的菜来。
这个问题解决了,大家还是高兴不起来。因为每个人觉得在这里读书,就是混个高中文凭,考大学的希望非常渺茫。于是,我们中有不少人开始退学,特别是我最要好的兄弟程同学跑到广西去当了兵,让我每天伤心得死去活来,比失恋的感觉还强烈。
我终于像许多人那样,选择了离开,在村里一位老师的帮助下,去了另一所大家认为更有前途的普通高中。离开时,我站在陡坡向镇上与河流望去,天空阴沉沉的,我的心里像灌满了铅一般的沉重。大家知道我要走,许多都站在身后送别,祝福声此起彼伏。许多年后我回故乡,听说这所学校被拆掉了。我找了好多人打听当年班主任的消息,想去看看他,结果却是不幸的:他因为心梗去世了。
新的学校在一个叫大赵家的地方,属于“二程镇”,也就是著名的宋代理学大儒程颢、程颐所在地,离我家有一百多里地。每次上学,我都是照例先走几公里的山路,来到我们附近的镇上。从那里坐车到县城,再从县城转车去学校,来来去去,几乎都得一天时间。因为没钱,我很少回家。每隔半个月,我母亲便托人把菜和米带到县城我堂兄的单位,我再从学校这边坐车到县城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