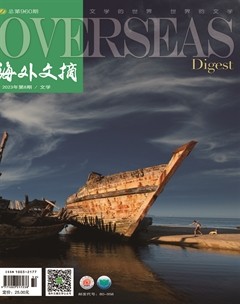一
为追寻明末清初那位天地大儒在永州的行踪,我与朋友们来到了双牌县境内的云台山。
山如台,云如带。云带绕山,似一幅水墨,果然是好山,好云,好风景!
此处,离双牌县城颇远,离永州市区更远。只有到了云台山这样的地方,才有置身世外桃源的感觉。
年少时,总是向往城市的繁华与热闹,总觉得只有站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才能感到自己真实的存在。
时至此时此地,方才醒悟: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没有回程的孤独之旅。一路前行,一路相逢,有聚有散,方为常态。
而这次,我们要在常态的人生中,追寻一个人往昔的“非常态”。他为什么来这里?在这里干了一些什么?若不仔细追问,似乎还有许多谜团无法解开。
在山路上,我一边听取当地村民的介绍,一边瞪大眼睛努力去探寻,期盼在某棵古树下、某条小路上,邂逅他渐行渐远的背影。
而在追寻的过程中,自己的心里忽然涌起一种“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感觉,渴望像古代君子那样,邀请我追寻的对象在此共圆一个隐居梦,抛却名利,在屋前栽花,屋后种菜,松花酿酒,春水煎茶。
只是今天,我能穿越时空,与三百六十多年前那位本名叫王夫之,后人称为王船山的大儒在此相遇吗?
春雨歇脚之际,云雾渐渐散开,前方的数座山峰现身而出,似出水芙蓉,十分美丽。只是不到片刻,云雾又缠绕而来,特别是一缕云彩,竟仙道般向我扑来,挨近时却又化成乱絮旋即随风而去。
我见了,心里一震:那是羽化的王船山吗?
可是他为什么却又马上离去了呢?难道是我的脚印凑巧重叠了他的脚印,因而惊扰了他栖息在此的宁静?难道当年他也是站在这个位置眺望远方的,因而带给今天的我某种心灵感应?
远方,有他的人生理想,有他的远大抱负,自然也有他的沧桑經历和心酸回忆。
是啊,他曾在此驻足眺望,没想到一转身却已三百六十余年。
想到这里,我脑海里忽然涌出一句汉诗: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在云台山寻寻觅觅,我耳畔似乎传来一个朗诵的声音:“佛宇不可知,云留高树里。日落钟磬声,随云度溪水。”
这是王船山先生写在这里的《云台山》诗,收录在他的文集里。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按图索骥,我找不到当年的佛宇、看不见当年佛宇里的佛陀身影,只在附近见到了一些残剩的寺庙遗址;侧耳倾听,再也听不到当年佛宇悠扬的钟声,只有注入附近潇水的那条溪水尚存,但也似乎瘦了许多;只有那变化多端的云,还似当年那般顽皮,仿佛要告诉我们船山先生当年栖息在此的点点滴滴……
二
据《王夫之年谱》记载:“国朝顺治十一年甲午(公元1654 年),明桂王永历八年,公三十六岁……秋八月,公避兵零陵北洞钓竹源、云台山等处,敉公留侍。”
永州学者张泽槐先生的《永州史话》亦有类似记载: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 年)八月,王船山避难于零陵北洞钓竹园、云台山等处。
从王船山留下的文字来推测,北洞钓竹源应当在祁阳县与零陵交界处,但现有地名中确实难以找到痕迹。所幸,《船山文集》中收录了他写的一首《钓竹源》诗:
杉竹迷千嶂,豆苗萦一湾。麇䴥不相避,肥草隐潺湲。
从诗中可以看出,钓竹源是一个风景秀美、生态良好的地方,很适合隐居。大约是追缉太紧的缘故,他不得不放弃。
而他在永州的第二个歇脚点云台山,在寂寞三百六十余年后,毕竟等到了我们这些探寻者的足印。
云台山在今双牌县上梧江瑶族乡,海拔八百余米,临近潇水,四周林木茂盛。晴朗之日,是看日出的好地方。
据双牌朋友和本地村民介绍,云台山曾有两座古建:一座是山顶的古庵,一座是半山腰的枫王庙。
遗憾的是,两座古建早就坍塌,只剩下些许残痕。
根据村民的指认,我们发现古庵的墙基还清晰可见,六个石头柱础散落在墙根,部分风化。在一户人家的走廊上,还发现两块被用作了台阶的青石板,上有模糊字迹不可辨认。
据介绍,古庵原有上下两栋殿堂和左右两排偏房,庵内有三口钟。庵内供奉着关羽像和十八罗汉,每逢农历初一、十五都有人来烧香。
而我的视线却聚焦在古庵遗址前的那棵大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