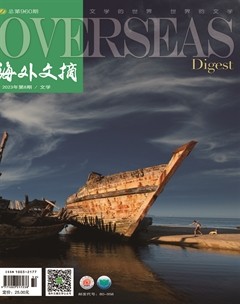1
2019 年的秋天是个什么样的节景呢,现在想想,那一天虹桥机场的上空蓝得刺眼,八月的暑热消退得有点儿慢,又或许是脚步匆忙的原因,即使是冷气开足的机场大厅,我只背了个包,脸上仍汗涔涔的。女儿推着她的三大箱行李,临登机时因超重不得不托运一个箱子。女儿总是在亲戚朋友面前说我在吃穿上从来没有亏待过她,正如我的父母亲从来不曾亏待过我一样,我认为“吃饱穿暖”是每个做父母给予子女最起码的生活保障。这三大箱衣物除了大学期间她认为比较得意的寥寥几件,比如大二那年她采访她中学时代的偶像许嵩时,穿的那一件裙子,是她节省了半个月的零用钱买的。一件大三寒假去香港实习时买的驼色大衣,她用了她那一学期的奖学金。其余小件如袜子、睡衣,大到冬天的毛衫、羽绒服,单鞋、靴子,都是决定动身前一周,我和她开车去了商城,逛了整整一天,从里到外,从上到下,置办齐全的,怕国外没有她穿的尺码。现在谈起来,觉得真是多此一举。但女儿说,这些带去的衣物,现在每季拿出来穿,仍然是她的盔甲,永不过时,不论出席哪个场合,都能合适地贴身并大放异彩。倒是她去苏州,去看她的室友兼死党,两人在飞猪上订票,悄悄飞去韩国看歌舞大赏,回来去了观前街,买的那一件丝质旗袍,她一直压在箱底,没有机会穿。
那天,没有电视剧或者小说里出现的动人桥段,我们彼此的胸腔没有任何感伤气味的充盈。相反,双方都有点儿迫不及待,她如雄鹰一样,野心勃勃正欲振翅高飞,而我亦欲如老牛般,半倚斜阳,准备卸磨归槽了。
女儿进了安检,我笑着问:“就这么上飞机了啊,没有什么话对我说吗?”矫情让我的体温迅速地降了下来,眼睛里落进飞机飞过上空投射到大廳天窗的阴影。
女儿隔着栏杆对我耳语:“寒假我就回国看你们。我不担心你以后的生活,因为你一直像土匪一样活着!”
“像土匪一样活着!”这句话像烙铁浸入沸水一样,水面上没有烫起任何烟雾。我云淡风轻地和女儿挥手,直至我不能越雷池半步,目不能所及。
尽管已有七八年的驾龄,我始终没有肥胆把车开向高速公路。这次送女儿,同样像以前去镇江南站接女儿,请人代驾,正好把车拉一下高速,清理一下出风口,这也成了女儿调侃我的一个话柄。她是第一个自告奋勇坐在我车子里的人,当我载着她在小城大街小巷龟速行驶的时候,我问坐在副驾驶位置的她怕不怕,她说不怕。她赞许道,你这个中年妇女能把车开动起来,值得表扬,这是你应有的样子!
2
那年的冬天是寂寞的,西北风剪了翅膀,除了在最初立冬的节气里喊了两嗓子,其他时间便偃旗息鼓。女儿从大洋彼岸倒是飓风般不停地发视频和图片,她们留学生也在宿舍里上网课,和合租的同学做黄油曲奇、芝士蛋糕。也有外出购物时,戴口罩的美国人和偌大的有点儿冷清的超市背景图。腊八那天,她却是做了个“腊八粥”,很是让我惊艳!她说全是凭小时候的记忆:坐在温暖的被窝里,喝着我一勺一勺喂进她口里的掺有糯米、红豆、花生、芝麻、红枣、桂圆、莲子、芡实等红彤彤的“腊八粥”,欢欣鼓舞,满怀期待,好像春节正热烈地向她奔跑跳跃而来!
“过年要有个过年的样子!”每到春节,我就会想起我父亲生前说过的这句话。院子东山墙上挂着一溜儿的腊肉与咸鱼,挨挨挤挤晒得往地下滴油;吊在廊檐口的风鹅、风鸡,把鹅毛管子剪下来,预备着做钓鱼竿的浮漂,好待来年开春坐在自家门口的码头上钓鱼;大公鸡又黑又亮的羽毛用铜钱串好,做成毽子,预备春节时拿出来踢,这比塑料皮剪成的毽子更加活泼灵动;摊在芦帘席子上热气腾腾的馒头,像孩子白白胖胖的笑脸,暄腾腾的、嫩簇簇的。红双喜坛子不见了,那是父母结婚时放在“老爷柜”上母亲的陪嫁,我们总会在后屋的稻积里挖到,那里面有炒熟的花生、葵花和蚕豆。我们自作聪明地偷食后,又悄悄地盖上盖子。
女儿对我沿袭父辈留给我关于春节传统的记忆,唯一赞同我的是每年春节临近,在客厅里养上一盆水仙花。她也不强烈排斥我在每个房间的门上贴上艳阳天色的春联,因为我和她说过,年画,尤其是带有故事情节的年画,是我混沌幼年最早最直接吸收的文化滋养。
女儿这代人,用她的话说,她们这辈人,注定是“故乡虚无主义”。从农村到城市,再从城市到都市,从都市到海外,她义无反顾地一路前行。
春节前几天,我们姐弟三人就在电话里酝酿怎样下乡拜年,规划拜年路线,先去三叔家还是先去姨妈家?在哪儿集合?谁人开车?他们一致地让我充当乘客。女儿却在年二十九晚上不断发来语音视频要求,劝诫我们不要下乡拜年。“新冠”这个词,第一次在我耳边出现,尽管这个词在三年后,或者以后很长时间会被雪藏,或者遗忘,但这两个字当时对于我们脑门的撞击,犹如冬雷滚滚。她说,怕我们担心,她瞒报了美国于国内早先爆发了大规模流感,多年在外求学,她养成了习惯,报喜不报忧。
自然,女儿没有履行寒假回来看我们的承诺,她的寒假已经结束了,所有关于春节的记忆全部在她的舌尖上复苏。她说想吃我做的烘得脆脆的、金黄透绿的豌豆饼,我就在视频里做给她看。她说她那里没有豌豆苗,去超市买了芝麻汤圆,汤圆委顿在电铛锅里,像盛开的糖糕,勉强可以敷衍过去。饺子终于包得有模有样,牛肉炖土豆,色彩艳丽。唯一遗憾的是,想吃家里的香肠,培根终究替代不了,少了一点儿阳光直射赋予食物生与熟渐变的灵动。除夕那天,她同校的留学生聚在一起,自制了红油火锅。桌子上,来自国内不同省份、各个地方的中国菜系大拼盘,摆放在桌子上,满满当当。我过去所有对年轻人的担忧,正如我青年时端午不吃粽子,中秋不吃月饼。在我中年后,节日的记忆,如磐石一样,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