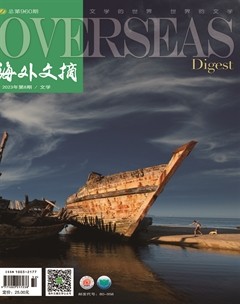?水河南岸的这个故事,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半个多世纪之前,我也才半岁吧!我的姥姥拿着我的尿布跳过㶏水边上的寨墙到㶏水河里去给我洗尿布,那时候的姥姥才50 多岁。她是后来人,不是我的亲姥姥。我半岁时,她来了,我的继母,就是我姥姥的女儿,是我父亲的第四位夫人,我母亲是第三位夫人,生下我之后,产褥热两个月就去世了。
我父亲是个工农干部,没有多少文化,16 岁参加革命,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48 年大部队南下,他从河北老家保定城跟随部队过黄河来到了河南,在㶏水河的边沿上有一小仗打,也许那一小仗在史册上就没有记载,可就是那一打土匪的小仗,他受了重伤,被部队留在了河南,留在了㶏水河畔的南岸。后来他做了㶏水河岸边一个叫邓襄镇(刚解放时叫邓襄公社)的镇党委书记兼镇长。再后来他做了郾城县的副县长、县长。邓襄是郾城县的一个乡镇。
那一天,他到一个乡中学去做报告,据后来他告诉我说那次报告是给中学里的学生们讲战争年代的革命故事,现在叫作演讲。他在讲台上把故事讲得激情振奋,底下听讲的同学们握着拳头热泪盈眶。我的继母就是那几百名听讲的同学中其中的一个,她比我的父亲小了十二岁,她来到我家的时候,我母亲刚刚去世两个月,镇政府的人看我可怜,我父亲一个大男人怎么也侍弄不好一个两个月的娃娃。据说当时是不少领导撮合,我继母来了,我姥姥也来了,我姥姥就我继母一个女儿,早年丧夫,29 岁就开始守寡,直到把我继母养大成人。姥姥开明,刚一解放,就把我继母送到了解放初期的速成班里学文化。
无论怎么说,我父亲的故乡很多,㶏水河岸边是他的第二故乡,却是我出生的故地和家园,我就是㶏水河畔的女儿,长大后我才知道,我父亲说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可我和我的弟弟妹妹们一张口就是㶏水河边的土味话。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啊!父亲16 岁参加革命,虽然生在乡野山村,却是个喜欢静思非常有头脑的人,随着他在部队的职务越升越高,他的文化素养也在职务的不断升迁中变化着,在部队转战的间歇里,他从不放过在忙碌中得到的少许时间,刻苦勤奋地读书学习,特别是不耻下问,得到了部队领导及战士们对他最公允的褒奖。父亲的家,也是我的老家,是在离北平城最近的地方,中国的中心,文化和经济命脉的中心,虽然那里大山一重又一重,河道一弯又一弯,却阻隔不断乡音在喉咙里低吟,父亲一口纯正的普通话,还有他此后在部队历练多年养成的思考习惯,即便后来从部队转业到了地方,那身刚正不阿的气韵也让人十分的敬慕。
我继母来的第二年,我大弟就出生了,我只比他大了一岁多点,我是这年的年尾,他是第二年的年尾。
我父亲走进市委大院里工作,我还很小,不记事儿,但也隐隐约约想起一点什么,比如:春天来临的时候,打开父亲办公室的后门,就会看见像花园一样的小径和万紫千红的花木,长长的柳叶垂在小径蓝色的砖沿上,有鸟儿的鸣叫,近处还有水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