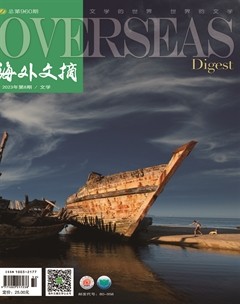我与刘策相识于1972 年合肥市文学创作学习班。
我是教师,他是一个十八九岁的现役军人士兵,经常利用业余时间请假来听我讲课。他酷爱文学,喜欢读书,那时他还没有开始写作。在文学创作学习班里他学得最认真,不迟到,不早退,埋头记着笔记。刘策悄悄地对我说:“我觉得这个学习班里有两个人今后有前途,一个是陈桂棣,另一个就是您。我很崇拜您,父母叫我拜您为师,好好学习写作。”听了他的话,我有点儿受宠若惊。后来陈桂棣写了《中国农民调查》一举成名,而我并没有出名。
有一天,他邀请我去他家,说他父母想见见我。他的父亲是个军转高干,时任安徽省交通厅厅长。他家住在合肥大东门那里省政府交通厅宿舍。虽然是高干家庭,但他家布置得简朴得体,与平凡人家别无二致。他的父母热情地接待了我,诚恳地要我帮助刘策学习写作。从此,刘策经常到我工作的学校去,我也经常去他家。听到他那高干父亲对我的赞扬,我心里像吃了他家蜜枣稀饭一样甜滋滋的。不久,文学创作学习班结束了。但刘策始终没有忘记我这个老师,节假日少不了来看我,实在没时间就给我写信。从他书信的字里行间,可见他对我的尊重和对文学艺术的竭力追求。
1975 年,刘策退伍了,被安排到合肥手表厂当了工人,开始写作并发表文章。有一次,他跑来找我说,《安徽青年报》搞“征文”活动,他想写一篇试试。他讲了个见闻:他正在大街上走,忽然见到一群人像蜜蜂一样聚集到一处。怎么啦?又出了什么事?我以为又是上访的人呢。走进人群注目一看,原来是一位中年男性师傅在做好事,帮助别人修理熄了火的摩托車。人们七嘴八舌议论他做好事,技术高超。他征求我的意见,想以这个见闻写一篇散文,不知道行不行?我大腿一拍说:“这个好啊!就以这个见闻为素材,写一篇散文。”后来他据此写了篇《星期天轶事》参加“征文”活动,竟然得了一等奖。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接连在省、市级,乃至国家级报刊上发表了许多小说、散文,还获得过合肥市青年文学创作一等奖。
刘策在手表厂当工人,看书写作的时间是有限的。也许是他酷爱文学感动了上帝,也许人生命运青睐了他,1978 年,他被借调到合肥市《文艺作品》编辑部当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