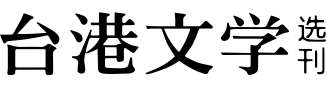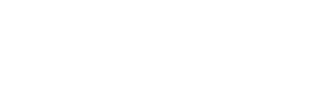妻子把我拎回家的鳜鱼清蒸了。青碧的葱花在汤面上游弋,鱼儿仿佛还活着,一双眼睛暴凸出来,热情洋溢地瞧着人。
女儿触景生情,背诵起张志和的《渔歌子》来:“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有一个故事在我们西吴市广为流传。说的是张志和当年在西吴一带做烟波钓徒时浮家泛宅,看桃花,钓鳜鱼,喝一种叫箬下春的土烧酒,最后醉眼蒙眬,从舴艋小舟上失足落入凡洋湖,溺水而亡。
妻子给女儿夹了一筷子鱼鳃上的嫩肉,笑道:“当年张志和在凡洋湖里得道成仙,变成了一条大鳜鱼。后来大鳜鱼生小鳜鱼,小鳜鱼再生小鳜鱼,鱼生鱼,崽生崽,一群群,一队队,游过苕霅之溪,来到太湖。天下鳜鱼出太湖,太湖鳜鱼出凡洋。凡洋湖是天下鳜鱼的老家,张志和是鳜鱼的祖宗……”
女儿嚷嚷说这故事外公外婆讲过一千遍了,老掉牙了,缠着母亲讲新故事。
我喝了一口鳜鱼汤,一缕鲜香在口中徘徊,我说:“我来讲一个新的吧,这是一个鳜鱼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人的故事。
“半年前,西吴市实施‘共富班车’工程,把公交线路从城里扩展到乡村,凡洋湖也通了公交,班车一直开到水波粼粼的湖边。这样,凡洋湖出产的鳜鱼运送进城更便捷了。
“开始时,是村里人往城里送。每天早晨头班公交车上,都是拎着大桶小桶鳜鱼的村民。车子从西郊进城,穿过整个西吴市,到城东公交车站,村民们拎着鱼桶沿途依次下车,显然经过了事先的市场调研和人员组织。他们有的来到菜场,有的送往饭店,也有的放在小区门口卖,城里人吃到了更新鲜的鳜鱼……”
女儿说:“妈妈就经常在小区门口买凡洋湖的鳜鱼。”
我继续说道:“村里领头的是一个漂亮寡妇,四十多岁,姓潘,村里老老少少都叫她潘姐。潘姐泼辣能干,每天清早组队从凡洋湖上车进城,晌午时分收队回村,一直到她在公交车上遇到了老张……
“老张退居二线后,闲得心慌,偏偏他又是个闲不住的人,那天在公交车上遇到潘姐,脑子里嗡的一声涌出许多灵感来。
“老张对潘姐说,以后你们不要每天进城了,这事交给我吧。我叫上一批退二线和刚退休的小老头小老太,每天到凡洋湖畔晨练,然后捎上鳜鱼,回城里送或卖。我们在城里工作大半辈子,人脉广,还能帮助你们拓展经销渠道呢。平时我们闲得慌,这样既有事可干,每天还能到凡洋湖畔呼吸新鲜空气,一举两得。潘姐说你们把活都干了,那我们做什么?老张道,你们就在村里负责把鱼养好。潘姐说,这是个好主意,你们要多少工钱?老张说,什么钱不钱的,我们有退休工资呢,这是我们老同志为西吴老百姓做好事實事,如果你们过意不去,时不时送我们一点新鲜鳜鱼吃就行了。潘姐听后,当场表态说,好。”
妻子插话道:“有一次我在小区门口碰到熟人在卖鳜鱼,还以为他退休后没事做赚外快呢,原来是这样。”
“不过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差点闹出绯闻来。”我说下去。
“大约一个多月之后,老张带着一群小老头小老太正干得热火朝天,妻子不知听到了什么风声,怀疑起老张与潘姐的关系来。这也难怪,一个半老汉子呼朋唤友,分文不取,帮一个徐娘半老的寡妇卖鱼,怎么解释也不能让人信服。老张越解释,妻子越怀疑,终于有一天,伸手在老张的脸上抓了一把。老张脸上挂了彩,第二天依然去凡洋湖,潘姐问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他坦然说是被你嫂子抓的。问为什么,答是怀疑我们俩有私情。潘姐是过来人,又泼辣豪爽,哈哈笑道,嫂子小气了,过几天我拎一桶鳜鱼去看嫂子……
“没料想就在次日清晨,老张去凡洋湖时,前脚刚上公交车,妻子后脚就跟上来,坐到了他身边。老张和她说话,她别过脸瞅着窗外,不吱声,弄得老张手足无措,车上那群小老头小老太一个个也紧张兮兮的,生怕老张妻子到凡洋湖闹事……”
妻子打断我的讲述,说:“看你讲得绘声绘色的,好像你亲眼看见一样。”
“确实是我亲眼所见,共富班车和我上下班同一条线路,我们经常在车上碰到。”我说着,夹一块鳜鱼,送进嘴里,一缕鲜嫩细滑的感觉划过喉咙,“你知道那个老张是谁吗?他就是我们单位的张局长。”
“后来呢?”妻子问道。
我指着桌上已经吃掉一半的鳜鱼,说:“后来,西吴城里一群小老头小老太和凡洋湖村民们一起成立了一个公司,专门养殖和经销凡洋湖的鳜鱼,张局夫妇是其中出资最多的。今天,张局给我们单位送来一车活蹦乱跳的鳜鱼,每人分了一条……”
女儿嘟哝道:“爸爸的故事跟张志和变成凡洋湖鳜鱼一样,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