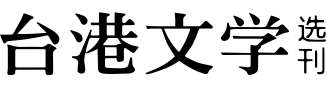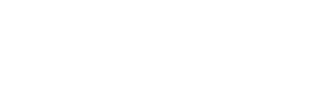小小说是平民艺术
小小说是平民艺术,那是指小小说是大多数人都能阅读(单纯通脱)、大多数人都能参与创作(贴近生活)、大多数人都能从中直接受益(微言大义)的艺术形式。小小说不仅具备人物、故事、环境等要素,还携带着作为小说文体应有的“精神指向”,即给人思考生活、认知世界的思想容量。之所以称其为“平民艺术”,当然不容忽略它在艺术造诣上的极致追求。小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创新,自有其相对规范的字数限定(1500左右)、审美态势(质量精度)和结构特征(小说要素)等艺术规律上的界定。小小说是平民艺术,除了上述的三种功效和三个基本标准外,着重强调两层意思:一是指小小说应该是一种有较高品位的大众文化,能不断提升读者的审美情趣和认知能力;二是指它在文学造诣上有不可或缺的质量要求。平民艺术的质朴与单纯,简洁与明朗,加上理性思维与艺术趣味的有机融合,极其本色和看得见、摸得着的亲和力,应该是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代小小说之所以能以民间读写的生存方式,永葆青春而长盛不衰,社会生活孕育的必然和人为努力的因素缺一不可。在诸多重要的小小说活动中,经常聚集了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小小说文体的开拓者、奠基人、实践者的代表性人物,表彰奖励,高端论坛,交流成果,生机盎然。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长期以来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相当自觉地参与其中,并在一定范围内组织小小说征文、笔会、理论研讨、出书评奖等活动,在文坛的名利场中泰然处之,潜心耕耘,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活跃在小小说读写市场,共同创造了一个令社会各界瞩目的小小说时代。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体
任何一个伟大作家乃至不朽作品,只有附丽于某种文体才能彰显其与众不同的独特文学价值。屈原、司马迁、李白、苏东坡、关汉卿、曹雪芹、蒲松龄、鲁迅等,莫不如此。以现实主义写法为主的《诗经》有很长的历史,但是当它后來逐渐淡出时,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楚辞就出现了,就是当一种文体不能满足社会读写需要或者是情感诉求的时候,必然会被一种新的文体所替代。再往后的乐府像《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等,把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以及叙事功能相融合,又成为一种新的文体,这都是社会文明、历史进步的标记。继而唐诗、宋词光华四射,流誉千年;从元曲的台上台下互动,百姓参与,叙事文学开始占据文学主流舞台;中国古代小说的鼎盛期或成熟期在明代已经形成,三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若加上《金瓶梅》“三言二拍”以及公案、传奇小说都出现了,无论笔记体写作还是白话小说写作,在长、中、短篇小说领域所取得的文学创作成就都达到高峰;清代可圈可点的有一长《红楼梦》、一短《聊斋志异》;现当代小说是文坛主流,从文体流变意义上讲,仍然可以看作是一种继承和发展。《诗经》、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文脉相承,皆为文体创新之最。
当代小小说是时代文体,经过多年的孕育已蔚然成林,荦荦大端,经典作品、代表作家、规范的理论体系和两代以上的读者认可,小小说正以一种新文体的独特身姿,跻身于社会文化建设中,赢得自己的尊严和荣光。从2010年小小说纳入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选系列,到2018年冯骥才以小小说集获得第七届鲁奖,再到今天的小小说作家王奎山的民间雕像揭幕等,对于小小说文体、小小说作品和小小说作家而言,都有着彰明丰沛的不可取代的标志性意义。
小小说的文学意义
在社会不断变革的每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国运文运交织,人们以文学的表现形式来抒发情感、解读人生时,大都会产生创新的欲望和冲动。面对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如有众多的人参与进来进行创作实践,并能相应地持续十数年、几十年或长达百年,必然会涌现出泰山北斗式的代表性作家和品质优良的经典性作品,这种生活孕育与人为因素的风云际会所自觉形成的文学读写,便会成为某种文学浪潮、文学运动乃至文学现象,甚至可以上升到一种具有宏大叙事的文学史意义的高度上来。3000多年以来的《诗经》、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现当代小说,文韵流传,各臻其妙,波澜壮阔,气象万千,不仅涌现出日月星辰一样耀眼的文学巨匠,而且构建了文学意义上的辉煌灿烂的里程碑式的时代文明。小小说文体的简约通脱、雅俗共赏的特征,决定了它是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小小说的读写不仅能为徘徊在文学边缘的人,拓宽大面积的文化参与和消费,圆了文学梦的情结,而且自身就携带着相当具有亲和力的文化权益。
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文学边缘化的今天,小小说这种精短的文学样式,在中国40多年的时间里在大众读写市场持续升温,从中不难看到:有矢志坚守、纵横开阖的倡导者、组织者的鼓与呼,有苦心经营的绩效优异的报刊、网络平台,有梯次结构分明的小小说创作中坚力量,有长期进行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的理论研究体系,有业界公认的专业领域的至高奖项,有两代以上读者的追随认可,小小说呈现出来的是一种与时代进步合拍的当代文化建设成果。无论现在与将来,小小说与小小说作家都会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个创新性字眼,必将载入文学史册。
文学读写的“三分法”
现在的理论界和评论界,喜欢两分法,要么谈精英文化,要么谈通俗文化,或者谈纯文学(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似乎忽略或回避了这么一个庞大的中间地带的契合点,即介于它们之间的那种既有精英文化品质、又有庞大文化市场的精神产品形态,即大众文化。譬如《红楼梦》是精英文化质地,因为曹雪芹在创作中调动了几乎所有艺术手段:深刻的内涵、曲折的故事、精密的结构、驳杂的人物以及言情状物、诗词歌赋等,注入了传统文化中最精髓的阳春白雪式的文化元素。《三国演义》《水浒传》是大众文化质地,语言晓畅,雅俗共赏,其故事属于地道的街谈巷议,茶余饭后、道听途说的“话本”而已。《西游记》则属通俗文化质地,稍显脸谱化概念化的描写,并没有掩盖它人物塑造丰满、想象多姿多彩、叙述妙趣横生的艺术光芒。无论是精英文化质地还是大众文化质地、通俗文化质地的文学作品,作品的表现形式与质量蕴涵,只要能完美统一,其实并无“孰优孰劣”之分,都能抵达艺术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