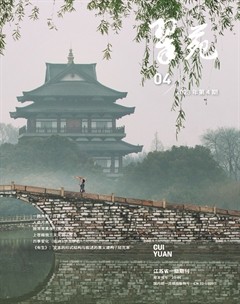一
时序又至癸卯年(2023年)。上推四个甲子,二百四十年前,曾生活在常州白云溪畔的一对生死兄弟真正阴阳相隔了。这是两个曾“京漂”的常州人。这一年三十八岁的洪亮吉,为三十五岁的黄仲则在山西安邑(运城)办了丧事。
乾隆四十九年(癸卯)二月,黄仲则被催债人逼迫,脚似铅重,拖着病躯离开京师,再度前往西安投奔陕西巡抚毕沅。一路翻越大行山,出了雁门关,始抵安邑(现山西运城)。病情加剧,实在走不动了,只得暂时住到老雇主河东盐运使沈业富官署中。这一路走来,仲则已典当尽自己的能当的一切,用来买药,终无济于事。知道自己大限将至,在官衙的一间客舍里,给远在常州的太夫人留下遗嘱,又给洪亮吉写信交代后事。沈业富当即差门人速送西安。
当这封“终以老亲弱子拳拳见属”的飞书传到入幕西安巡抚府的洪亮吉手中时,已是多日后的一个三更天。
毕沅巡抚也是好义有担当的人,当即借官衙驿站快马,让洪亮吉上路。洪亮吉纵马疾驰,一天跑过四个驿站,七百里加急狂奔四天,赶赴与陕西一河之隔的安邑,终是跑不过死神的脚步。沈业富已将黄仲则遗体移至萧寺安顿。萧寺,佛寺庙宇的别称也。即使朋友能容黄仲则在官署咽气,却也断不可在盐运使官衙内办丧事的。洪亮吉踉踉跄跄进得僧舍,但见门内遗体僵直,遗篇断章留在竹筪里,零星飞纸,狼藉几案。洪亮吉哭恸于灵前,昔日如鹤长身立于同伴的黄仲则终是去了。去世那一天是四月二十五日。
安邑是国朝盐都,朝廷在此设河东盐运使。沈业富从安徽太平知府转任此职。沈是江苏高邮人。高邮处苏中,和常州不过一江之隔,同为江苏人。沈业富是读书做官的通才达人。少有才名,科场顺遂。乾隆十九年中举,次年就中进士,才二十二岁,弱冠刚过。沈业富担任安徽太平知府时,聘黄仲则入幕担任儿子的老师。同时被聘的洪亮吉和黄仲则成了幕中同事。
年过半百的沈业富是怜惜仲则之才的,对生涯困顿、仕途蹭蹬的才子诗人是厚道的。先为黄仲则发文告殡,出资办丧,后又为其出诗集。丧期里曾一日三出官衙赴萧寺,亲为治丧,不遗余力。洪亮吉临出西安时,陕西巡抚毕沅、陕西按察使王昶均有厚赙,用以丧葬及奉养黄仲则老母,抚恤遗孤。
洪亮吉写成《挽联》,下定了扶灵送君回家的决心:噩耗到三更,老母寡妻唯我托;炎天走千里,素车白车送君归。
二
五月上旬,洪亮吉启程南下。从风陵渡过黄河。亮吉因叔父“留滞汉口”,要搭他的顺风船,便取道襄阳,抵汉口,顺江而下,取水道返常。毕竟千里炎天扶灵归乡,只得晓行夜宿不停歇了。这一路风沙浩茫,山路曲折,酷暑难耐,艰辛无比。“重然诺”的洪亮吉心中装着亡友的重托。
这返常归程跋山涉水,路途漫漫。洪亮吉脑海里始终抹不去和黄仲则一生交往的点点滴滴。他俩是在常州城中白云溪畔长大的发小。白云溪是一条美丽而又繁华的城中河。河岸绿树荫翳,烟火千家。每逢端午节,常州府会在此举办龙舟赛。其时两岸人声鼎沸,人潮如龙。黄仲则有诗言说两人过往:君家云溪南,我家云溪北,唤渡时过从,两小便相识。并反复强调:我家君家不半里,中间只隔白云溪。他俩有太多相似之处。都是幼年失怙,洪亮吉五岁父亲病故,仲则四岁父病亡。都靠大家闺秀的母親含辛茹苦养大并亲授读书,才没有荒废学业。
他们相逢于江阴旅舍,因共习汉魏乐府诗而正式订交,从此俩人成为不离不弃的终生好友。当时洪亮吉二十岁,黄仲则十七岁。这是乾隆三十一年发生的事。同一年,两人双双入龙城书院拜邵齐焘为师。龙城书院是常州八邑子弟的读书场所,当时常州知府潘恂特聘乾隆七年进士邵齐焘任龙城主讲。邵先生曾任翰林院编修,又两任顺天乡试同考官。以骈文负时誉,他的应试文已刊印作天下士子应考范文,是乾隆朝唯一能打通骈散文体的一个高手。洪、黄两人一入龙城书院就受到邵先生重赏,称赞为“常州二俊”。于是这对订交之友又成同门学子。洪亮吉得邵先生骈体文真传,黄仲则习得作诗妙法,自此两同门情谊日生,学业大进。
黄仲则出名较早,九岁到江阴县应童子试,蒙被吟出“江头一夜雨,楼上五更寒”,此为诗名之始。十六岁应童子试,三千学子中获县试第一,受到常州知府潘恂、武进知县王祖肃格外赏识。十七岁到江阴参加院试,补为常州府博士弟子员,成为秀才。洪亮吉十五岁起应童子试,屡试不第,至二十三岁方录为县学附生。
洪、黄两人虽出生于读书人家,但均因早年失怙,家道早已中落,实为城市贫民人家。洪亮吉依靠一母三姐纺织及做针线活过日子,早早走上了边教书边读书贴补家用教馆之路。黄仲则家有薄田,也只够勉强度日。成年后的他们便离乡背井,走上了入幕求生、乡试求名、游学赋诗的艰难生存之路。
文人游幕是清代一种极为普遍现象,康熙乾隆时期文人游幕盛极一时。清代幕客没有官职,与雇主是雇佣关系。幕主既是地方大吏,本身又是有名学者或文学家。他们进入督抚衙门或郡县府中佐理事务,处理文牍,批阅试卷,编撰地方史志等。洪、黄两人先后在太平知府沈业富、安徽学政朱筠幕中同为幕宾。他们作为高级打工同事,其才能被朱筠称为“龙泉太河,皆万人敌”,以“猿鹤”喻之。
洪、黄两人虽有同乡、同门、同幕等相似之处,但性格脾气、处事方式等却迥异。一个谦恭,一个狂傲;一个厚重,一个敏感;一个忍负合群能扛事,一个一言不合就任性。按理说,怎么着都不可能是生死兄弟,只能说人与人的相处是很主观的东西,一眼看过便相信而接受了对方。他们经历过的生存苦难,在他俩成长过程中产生过共性的觉醒感悟,使他俩成为一生的异性兄弟。但性格决定命运。洪亮吉自视中材,一生勤勉忠恭,深得雇主赏识。就像一条孺子牛,日日劳作;凭一支笔,写出了自己的生活坦途。黄仲则恃才傲物不合群,家贫自卑,多愁自怜,多病敏感,为人所难容。诗虽工而人生道路却越走越窄了。
三
山一路,水一程;千里山水,千里云月。过往的影像一帧又一帧,很多都是两人共同经历过的。行至宜阳,在逆旅中“知君最详”的洪亮吉,回溯过往,泣血写成《国子监生武英殿书签官候选县丞黄君行状》,为后人留下最真实的黄仲则事迹。
这篇行状的前缀,正是国子监生黄仲则“京漂”九年的奋斗实录。乾隆三十九年八月,洪、黄共赴江宁乡试,又不中。十月一同前往常熟,凭吊恩师邵齐焘。那次傍晚时分登上虞山,游罢仲雍祠,北望先生墓,黄仲则思虑再三,对洪亮吉说:懂我的邵先生死了,如果不幸我死在你前,你能像湖南按察使王太岳帮恩师刊印《玉芝堂》那样为我刊印诗文集吗?洪亮吉感到当时仲则言语错乱无序,不作正面回答。黄仲则焦急地拉着洪亮吉衣襟,把神祠香烛点燃,执意要洪亮吉应允。黄仲则以二十六岁年纪竟作如此不吉利安排托付,虽属异数,实则是家族悲摧短寿的宿命一直纠缠着他。仲则十七岁取得秀才资格那年,同父异母的哥哥二十五岁就去世了。父亲和哥哥过早离世,显现家族命运的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