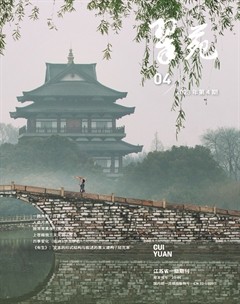一
尽管小说文本与生活世界牵拽着繁复的实在性关联,但就其本质而言,小说文本乃是创作主体建构的艺术世界,是一种主体建构物。如何建构小说文本?这问题是小说家无法绕避而必得解决的。在《有生·后记》中,作者胡学文坦陈:他的创作曾一度烦难于“小说的结构问题”和“叙述视角的问题”而“迟迟没有动笔”①。其实,结构和叙述视角均为小说文本建构的要件,胡学文最终以“伞状结构”处理前者——那是某个雨天他撑伞散步时“突然受到启发”,灵感来临“那一刻”他“欣喜若狂”②;至于后者,他虚构祖奶作为小说主角,以第一人称铺陈其故事,且另行布设五个次要人物(如花、毛根、罗包、北风和喜鹊),他们的故事以第三人称展开。作者如此概括他对小说结构和叙述视角的处理:我让祖奶不会说,不会动——请她原谅,但她有一双灵敏的耳朵。小说写了她的一个白日和一个夜晚。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她讲述了自己的百年人生。另外五个视角人物均是祖奶接生的,当然,祖奶和他们不是简单的接生和被接生关系,他们如伞柄和伞布一样,是一个整体。③
作为主体建构物,小说文本建构自然受制于作者的创作动机和创作意图。《有生》对结构和叙述视角的处理,肇因于作者的创作雄心,他自述:“我一直想写一部表现家族百年的长篇小说”,并且,不愿重复家族小说的既有模式,而要“换个形式,既有历史叙述,又有当下呈现,互为映照”④。小说中祖奶的形象塑造及其故事演绎,正呼应着“表现家族百年”的创作意图,乔大梅流落塞外而生根宋庄,百年坎坷的确具备家族史的磅礴容量。叙事取祖奶自述方式,其一世沧桑于一昼夜间倾吐而出,叙述视角的巧设在此显出匠心和灵气。小说上、下两部各十章,交错展开祖奶故事和五位次要人物故事,外在结构既呈对应关系,叙述内容则体现着“历史叙述”(祖奶经历)与“当下呈现”(如花等五位人物)“互为映照”:作者的创作意图就这样落实在他的叙事实践中,成为文本建构的要件。“伞状结构”委实是一则生动比喻:作为情节主干的祖奶故事犹如“伞柄”,五个次要人物故事就像“伞骨”附着其上,撑开便成“伞布”。如此文本建构匀称而整齐、端庄又简练。也有论家命之为“坐标系艺术结构”或“树状结构”,各执理据,俱有妙处。
但我更愿意将《有生》的文本形制,概括为“丛生结构”。祖奶故事的外围,伴生着五个次要人物故事,构成主次有别而有序的“故事丛”,恰如一簇生机郁勃的丛生植物。并且,细心查究小说叙事构造,更可发现其呈现为多重故事丛有机聚合的丛生结构。祖奶故事与五位次要人物故事,构成“主干-伴生”故事丛,形成叙述的整体框架,可称为“总体性丛生结构”。值得注意的是,总体性丛生结构不只是外在的形式结构,如花等五人既为祖奶接生而带入现世,更与祖奶存在“祈求-训谕”关系,具有内在的情感-精神关联,此层深在蕴含遂使总体性丛生结构具备意义建构的性质。而在总体性丛生结构中,人物故事也多有关联,即此形成“微型故事丛”,可称“局部性丛生结构”。如花与钱玉,毛根与宋慧,罗包与麦香、安敏,喜鹊与父亲、弟弟、丈夫黄板及乔石头,杨一凡与养蜂女……人物故事勾连、缠结,丛生成簇。便是祖奶自述中,其三任丈夫、九个子女的故事,黄师傅及其儿子的故事,李二妮及其丈夫的故事,李贵的故事,宋庄钱家故事……它们起伏错落、断续交接。人物故事单元既具有相对独立性,相互间又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由此呈现出故事丛聚合的丛生结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丛生结构正反映出乡土社会人物关系的原生态构造。
概言之,《有生》的文本叙述表现为总体性丛生结构和局部性丛生结构的有机结合,呈现出多重故事丛有机聚合的结构。这不仅是小说外在的形式结构,还表现着人物间的情感-精神关联,反映着乡土社会的原生态构造,因而具有意义建构的属性。
二
论家多强调《有生》具备“史诗”品格,证说也各执据理。但《有生》的历史叙述有意避开对历史内容的直面描述,自觉淡化对时代政治的直接表现,历史内容和时代政治被审慎地置于小说叙述的“背景”。对此,作者本人抱持着明确的创作意识,他说:我当然不打算写成历史小说,也无意把其中一段截取出来,放大讲述。历史只是作为背景,但这个背景不是虚无缥缈,而是真实的存在。小说从清末至20世纪初,至伪蒙疆政府,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革开放,直至新世纪之后,百年的跨度,每个节点对个人命运都有所波及。但在叙述中,我没有把历史具象化,虽然是真实的存在,可依然作为背景处理。⑤
将历史内容和时代政治“作为背景处理”,其实是将之融于人物故事中表现。乔秋对“油饼”无法遏制的渴望,映照出饥饿时代民间社会的普遍困境,其连篇累牍的“大话”“吹牛”,无不纠结于一个欲望焦点——食物,画饼充饥正是匮乏年代的辛酸表征。变革计划体制的社会转型,作者无意在叙述中铺陈、渲染,只在营盘镇“商店”变迁的简约交代中暗示——
营盘镇有三个大商店,副食、百货、五金,在用布票、粮票、肉票的年代,商店的门槛都油光锃亮,若要买一辆自行车,须主任批条子才行。后来不大景气,终至关门。罗包把副食店租下来,简单改造,挂出罗家豆品的牌子。
“须主任批条子才行”,一语道尽当年计划体制的无限风光,但其全副矜持逐渐转向无奈,它最終坠入“关门”绝境。私营个企先是以“租”的方式取而代之占据铺面,几年之后罗包索性将营盘镇食品公司连房带院买下,“将老房推倒,盖了座二层楼。左边开饭店,右边磨豆腐”。这是营盘镇商业变迁的一幅素描,历史内容和时代政治隐现其中。罗包“发家致富”的故事分明包含着重大的时代主题,但作者无意彰显此间的时代政治蕴含。他有意避开“意识形态的追光灯”,而专注于人物(罗包)形象塑造。对此,作者本人具备高度的创作自觉,他说:“人是小说的核心,作为背景的历史是人的窥视”,因此其叙述“没有把历史具象化,虽然是真实的存在,可依然作为背景处理。既然非重点,就没有必要浓墨重彩,以免喧宾夺主”⑥。
当作者自觉地将“历史”作“背景”处理,并专注于小说人物表现,人物及其生活世界的日常性便凸显而出,成为小说意义建构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