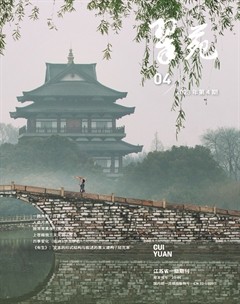艾芜于1935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南行记》,共收入8篇小说。“在左翼革命现实主义流派之内,发展起一种充满明丽清新的浪漫主义色调与感情、主观抒情因素很强的小说。”[1]然而,浪漫主义色彩,边地人民形象,地位、遭遇等通常备受关注的内容,都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南行记》是艾芜最突出的短篇集,以一个漂泊知识者的眼光观察并叙述边疆异域特殊的下层生活,刻画出各式各样具有特殊命运的流民形象。”[2]小说中的叙述者——流浪的读书人“我”才是故事中最让人感兴趣的形象,其独特的叙述模式更值得我们深思和探讨。
《南行记》的行旅主题
《南行记》中的第一篇《人生哲学的一课》最为集中鲜明地塑造了叙述者“我”这一流浪读书人坚强、刚毅的形象,一改以往知识者感伤、忧郁的“零余者”的精神软弱,也拉开了“我”流浪旅途的序幕。“我”漂泊到昆明,投宿在一家鸡毛店,与一个生疳疮的人同睡一床,之后又遇到了一个有着难闻足臭的旅伴,为了填饱肚子,卖草鞋,想拉黄包车,打算去工厂做学徒,但都不成功,最后因鞋被偷与店老板争吵,而被赶出店外。小说篇末那句“就是这个社会不容我立足的时候,我也要钢铁一般顽强的生存!”[3],无疑是“我”在南行中的誓言,为整部《南行记》定下了一个情感的基调。在以后的各篇作品中,处处都能使人体味到这种顽强与不屈。也为我们概括出了叙述者“我”的总体精神取向:坚忍、勇敢、善良、乐观。正是如此,“我”在山峡中成功救下了野猫子;在松岭上,取得了老爹的信任;在茅草地,撑过了被骗去做苦力的日子,而艰苦的磨难并没能麻木“我”的心,依然怀着强烈的同情心和正义感,讽刺嘲弄所谓的洋官;愤愤地大骂“老鬼哪!我诅咒你那末一笑!”[4],原谅了那个手脚不干净的“我们的友人”;对那个“永别的爱人”怀着无限的悲悯。《南行记》中的8篇小说各自独立,但每篇作品都以“我”在流浪漂泊中人、事的奇遇开始,又以“我”最终总会选择离开而收束。“我”是一个叙述者,也是旅行者,一个不断行走的“讲故事的人”,因此分别独立的篇章就通过“我”这一贯穿始终的人物形象串联起来。于是整部《南行记》叙述呈现出一种“入—出—入”的结构,这像是一条两端无限延伸的直线,而其中每一篇小说的叙述只是截取其中的一部分,“我”为什么要流浪,“我”如何与这些人相遇,离开后又要去哪里等等内容,在作品中都省略不述,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遐想,拓宽了叙述的延伸空间,有一种行旅的神秘感和未尽之意。这就构成了《南行记》“旅行者叙述”的基本结构。
这种“入—出—入”叙述结构的形成是因为作品所取主题的特殊性——行旅。同时这是一个积淀着我们这个民族传统历史文化心理的文学创作母题,也是一个贯通古今的诗题。大部分传统行旅文学不管是叙事还是写景,都是意在抒情,最后往往归结为抒发羁旅之苦、怀乡之思,和对前途茫然惶惑之感。这时的“行旅”主题主要蕴含着漂泊者沉重的离情别绪,在漂泊的行旅中,生命本身的价值和意义未能得到深刻的揭示。但是,行旅与生命是息息相关的,行旅的每一步也是生命中的一个历程。传统行旅主题的作品里多是一个被动承受痛苦和无奈的抒情主人公自我形象,还未能将其抽象化、象征化,成为生命主体在精神和理想上自为的追求。“直到21世纪初,这一缺憾才在中国现代作家那里得到了弥补。在中国现代漂泊母题文学作品中,表达离情别绪这一传统的创意与叙事固然被继承下来,但许多作品显然已把表意的重心转移到漂泊者生命本身的活动上来,一曲曲生命意志与生命力量的赞歌引人入胜,成为现代漂泊母题文学最为重要的子题之一。”[5]
于是,《南行记》中的行旅主题与传统行旅主题的区别就在于这里的“旅行”或“行旅”不再是简单地与“家居”相对,也不是一种被迫的流亡或出走,而是一种主体内心深处主动的自我精神放逐。首先具有一种流浪意识:永不止息的追寻,对社会、人生超越性的观照。因为小说文体的虚构性,所以不能将作品中的“我”完全等同于作家本人,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南行记》中“我”的经历与艾芜本人的流浪经历极其相似。作品具有浓烈的自叙传色彩,“艾芜富于传奇色彩的南行经历无疑是小说最主要的现实素材和情感基础”[6],因而不能不分析艾芜现实存在的南行经历的原动力。艾芜南行的直接原因或许是外力的压迫,如为逃婚、为求学等,“仿佛一只关久了的老鹰,要把牢笼的痛苦和耻辱全行忘掉,必须飞到更广阔、更遥远的天空去一样”,“才能抒吐胸中的一口闷气”[7]。但当我们进一步追问南行动机时,便会陷入困惑。他为何会选择偏僻蛮荒的云滇边陲?这恰好说明艾芜的南行是一种主动选择,而且是内心深处真实欲望的需求,“蜀中沉闷、痛苦和耻辱” [8]只是艾芜决意南行的一个导火索。而且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了解南行的生活是难以想象的艰辛、窘迫:饥饿和疾病的折磨,旁人的冷眼、嘲弄,甚至随时都有性命之忧。但艾芜却对南行始终兴味盎然,以至于归来后,仍梦绕魂牵,“先前漂泊过的生活,便常常象梦也似的,回到我孤寂的心上来了”[9]。1961年和1981年,在艾芜57岁和77歲时,又进行了两次南行。“对于艾芜而言,‘南行’不只是一种题材选择,而是一个自外于‘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神往漂泊的知识者的思想外化,云南边地亦不只具有地理学意义,而暗含着一个疏离现实生活的精神彼岸、精神异乡,这是20世纪30年代艾芜书写《南行记》的原动力。”[10]唯其如此,我们方能理解艾芜故地重游时“那份如鱼得水的逍遥,那种生命力勃发的销魂”[11]。南行的苦难历程没能让艾芜意志消沉,反而获得强大的行动力量,他早已陶醉其中。对于艾芜而言,南行更是一次精神之旅的象征。此外,《南行记》中的行旅主题更具有在独特的生存环境中体验到的独特的生命意识。这就迥异于以标异与炫奇为特点的,如近代《镜花缘》《老残游记》一类的小说,虽“其人物环游海外,其事件无奇不有,却很难被当作漂泊母题文学来研究,充其量只能说是志异之作,其原因就在于这类作品缺乏作家主体精神的浸润,缺乏漂泊母题文学所要求的心灵性品格”[12]。选择以《人生哲学的一课》开篇,想必对作者而言,这是《南行记》中“我”不屈不挠的主体意识的高扬。在“五四”思想解放的激进热潮中,描写反抗封建制度的束缚、黑暗社会的压迫,选择出走以寻求光明前途的作品盛行一时,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中的“出走”主题。而对“出走”之后的最终结果,鲁迅曾深刻地揭示出了两种可能:要么堕落,要么回来。然而,《南行记》中“我”的行旅,却是“铁屋子”之外的另一选择。面对生存的危机和压迫时,“我心里没有悲哀,眼中也没有泪。只是每一条骨髓中,每一根血管里,每一颗细胞内,都燃烧着一个原始的单纯的念头:我要活下去!”[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