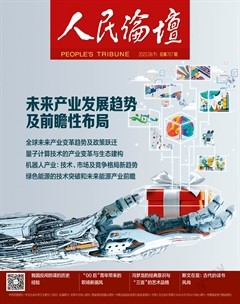【关键词】脑机接口 伦理难题 发展前景
【中图分类号】R318 【文献标识码】A
脑机接口(Brain-Computer Interface,简写为 BCI)是与人工智能关联的当代前沿技术之一,它在人或动物大脑与计算机及其外部设备之间建立起信息交换的联系,可用于辅助、修复或增强人的行动、表达和感知功能,从而可以帮助肢体残疾者重新获得一定的运动能力、帮助失语者重拾语言表达能力以及帮助感官失能者(如盲人、聋人等)恢复一定的感知功能。除了医疗健康领域之外,脑机接口技术还可用于艺术、体育、军事和游戏等场景,展现出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
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现状
从1924年作为脑机接口萌芽的脑电图发明算起,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已有近百年历史。进入21世纪后,这一技术逐渐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其应用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如2005年美国布朗大学神经学家约翰·多诺霍带领的“脑之门”(BrainGate)研究团队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在九位病人中进行了第一期侵入式脑机接口临床试验。其中,纳格尔(Matt Nagle)作为一名四肢瘫痪的残障人,研究团队在纳格尔脑中植入了包含96个电极的“犹他阵列”(Utah array),纳格尔由此成为第一位用BCI成功控制电脑光标的受试者,这为后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参考。2011年4月12日,在BrainGate实验室里, 58岁的瘫痪女子哈钦森(Cathy Hutchinson)在脑机接口的帮助下用自己的“意念”控制机械假肢拿起一瓶咖啡送到自己面前,并用吸管喝到了咖啡,这被认为是一次重大的突破,因为这是人类第一次通过“意念”来控制机器手臂实现了物品拿取和自我喂养等动作。2014年6月,高位截瘫的青年球迷朱利亚诺·平托(Juliano Pinto)在巴西举行的世界杯开幕式上,用自己的“意识”通过脑机接口控制穿戴在身上的仿生机械外骨骼,开出了该赛季具有象征意义的第一球,作为“重拾行走计划(WAP)”的脑机接口成果,被全球大约12亿观众所见证。2017年4月19日,Facebook在F8开发者大会上展示了自己下属的一个部门Building 8所研发的“脑机语音文本接口”(brain-computer speech-to-text interface),简称“意念打字”或“大脑打字”,即通过脑机接口设备让人可以仅仅通过默想自己说的话就能打字,从其展示的一段实验录像看到,一名女士(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患者)在没有讲话且没有敲键盘的情况下,通过脑机接口将计算机光标移到屏幕上的虚拟键盘的相应字母上,每分钟可以打出8个字,从而通过脑控打字的方式将大脑中的想法直接展示在计算机屏幕上。他们还宣布了自己的目标是研制出每分钟可以直接用大脑输入100个单词的系统,这将比人们用智能手机打字的速度快4到5倍。
从技术路径上,脑机接口分为非植(侵)入式和植(侵)入式两种,两相比较各有优劣。前者无需手术,只需将采集脑信号的电极附着在头皮上,其风险小但探测到的脑信号精度不高,所以实现的功能不多,只能用来执行简单的控制或操作;后者通过手术将电极直接植入到大脑皮层中,因其离神经元更近,可以获得更高质量的神经信号,但其因需要手术操作,故有风险,且成本较高。因此,目前的脑机接口主要采用的是非植入式技术。对于那些重度瘫痪者(四肢均无行动能力),通常需要植入式BCI才能恢复一定程度的行动能力;对于感官失能者也需要植入式BCI才能恢复相应的感知能力。
植入的技术路径目前也有多种,一种是犹他电极的植入技术,这是一种硅基硬质电极,通过开颅手术将其置于大脑皮层表面,作为电极的96根钢针就是记录96个神经元的通道。另一种是“血管介入式”的支架电极技术,它通过静脉血管将电极放在脑中的主血管里,隔着血管来采集脑电信号,它不像植入犹他电极那样需要开颅而只需“微创”手术,但由于只有十几个通道,所采集的信号范围有限,只能用来实现非常初级且简单的任务。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创立的Neuralink是世界上非常著名的脑机接口研发机构,他们采用的植入技术路径是不同于以上两种的“柔性电极系统”,通过自行研发的俗称“缝纫机”的设备,将比头发丝还细的电极直接植入脑中相关部位,较之硬质电极的植入创伤更小并能有效降低大脑的排异反应,其通道数目前可以达到1024个,以后还可以实现上万甚至上百万的增长。Neuralink的这一技术路径已在动物实验中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如2022年12月在公司的发布会上展示了一只植入脑机接口的猴子可以用“意念打字”,但用于人体试验的申请一直未获FDA批准。在进一步完善方案后,2023年5月25日,Neuralink表示它们所申请的人体临床试验已获FDA批准,并将在6个月内开始这一试验过程。Neuralink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脑机接口技术系统,他们对脑机接口技术进入公众视野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这意味着一支更大的团队将用更好的装备和技术路径去攻克BCI的难关,一旦取得突破性进展,将对植入式脑机接口技术的成熟和推广起到重要作用,也使公众接受这一技术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从而为脑机接口的大规模人体应用、甚至走向增强性应用开辟道路。因此,这一申请获批的意义重大,甚至被称为“里程碑事件”。
脑机接口技术不仅有着广泛的现实用途,还包含难以估量的潜在价值,因此,一些发达国家纷纷将其视为战略高地而列入优先或重点支持的创新领域,这方面的研究机构和团队不断组建,他们中较为著名的有安德森(Richard Andersen)、多诺霍、肯尼迪(Phillip Kennedy)、尼科莱利斯(Miguel Nicolelis)和施瓦茨(Andrew Schwartz)等人的研究团队。①尤其是在2016年埃隆·马斯克创建Neuralink前后,世界各地诞生了大量的脑机接口创业公司,IBM、高通等科技企业巨头纷纷涌入这一领域,国内也涌现了如博睿康、宁矩科技、脑陆科技、强脑科技(BrainCo)等脑机接口研发公司,当然还有不少国内研究机构和大学(如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的脑机接口研究团队和实验室相继成立,并不断取得研究和實验进展。由此,脑机接口的研发已经成为“一个爆炸式增长的领域,涉及遍布世界几百个研究团队。BCI的研究令人兴奋,而且其潜力吸引了许多年轻的科学家与工程师进入这个充满活力的群体”② 。在这一背景下,作为脑机接口技术当代开创者之一的米格尔·尼科莱利斯甚至认为:“一个脑机接口的时代即将到来。”③
脑机接口技术在发展中需要攻克的难题
脑机接口技术虽然发展迅速,但也存在许多有待攻克的难关,其中既包括技术本身的难关,也包括人文社会方面的难题。
首先,在技术上,目前的脑机接口还有许多技术局限,尤其是受信号获取的难度和精度的限制,使得如何处理嘈杂的电信号、获得更多更准的脑信号,成为需要攻克的首要技术难题。大脑是一个复杂的生物器官,所产生的脑电信号非常微弱,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与人的意图和思想有关,且常常受到噪声的干扰,因此,需要研发有效的信号滤波和特征提取技术,来准确地采集有用的信号。此外,由于不同人的大脑结构和功能具有差异,因此,还需要寻求更加个性化和更具适应性的信号采集和分析方法,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信号的准确性和实用性。植入式BCI与非植入式BCI相比,虽然可以获得更准确的脑信号,但植入的电极可能会引起免疫反应和组织损伤,由此导致植入的电极在时间上的不稳定性和脑组织的退化,同时引起脑电信号质量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