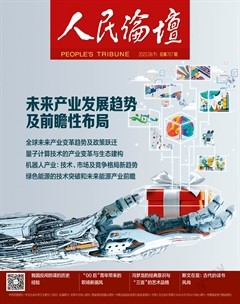【关键词】话本小说 “三言” 《喻世明言》 《警世通言》 《醒世恒言》 经典价值 艺术品格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三言”是人们对明代小说家冯梦龙所编《喻世明言》(《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话本小说集的通称。这三部小说集既收录了宋元话本小说(可能经过明人、包括冯梦龙不同程度的修改),也有明人创作的作品。无论宋元旧篇,还是明人新作,“三言”的总体水平在当时就得到了很高评价,如即空观主人(凌濛初)在《拍案惊奇叙》中说:“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而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不知一二遗者,皆其沟中之断芜,略不足陈已。”①从这样的角度看,“三言”不仅是冯梦龙所编辑的畅销书,也是他对话本小说作的一次经典化工作。在明刊“三言”前面,各有一序,尽管署名不一,一般认为都出自冯梦龙手笔。三篇序文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但反映了冯梦龙话本小说经典意识的连续性与逻辑性。而他所作的编撰工作,则是其经典意识的体现与落实,这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典的筛选,二是对筛选或新创的作品作精加工,使之成为名符其实的经典。可以说,冯梦龙的经典意识与“三言”的艺术品格是密不可分的,是我们把握“三言”基本价值的关键所在。
对话本小说文体特点的清醒认识与自觉把握
冯梦龙编辑“三言”,反映了他对话本小说文体的清醒认识与自觉把握,这首先表现在对小说的本质属性、也就是所谓虚构与真实性的论述上。
真实性一直是困扰中国古代小说家的一个问题,通常的思路是指出小说可以“羽翼信史”,具有“野史”的功能。这种依傍史官文化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小说家的文体自信,但不可能从根本上减轻主流文化对小说的歧视。关键在于,这样的说法没有揭示小说的真正的、独立的特点。冯梦龙在《警世通言叙》中,从话本小说发展的新高度出发,明确指出小说创作“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其真者可以补金匮石室之遗,而赝者亦必有一番激扬劝诱、悲歌感慨之意。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②,强调“触性性通,导情情出”之“理”,而不是单纯的客观之“真”,正是冯梦龙经典意识的核心。换言之,冯梦龙将真实性问题转化为小说对社会大众的艺术感染力问题,他在《古今小说叙》中甚至将话本小说的感染力置于儒家经典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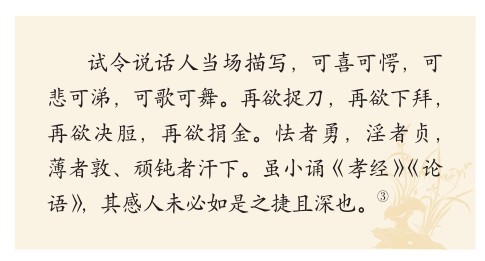
《警世通言敘》中还借《三国演义》中关云长刮骨疗毒对“里中儿”创其指而不呼痛的激励,形象地说明了小说巨大的感染力。
因此,在“三言”的编辑中,冯梦龙显然对那些能够激发读者共鸣的作品更为赞赏,如《范巨卿鸡黍死生交》描写了范巨卿与张元伯之间旷古难寻、流芳百世的友谊,除了进一步丰富这一传统题材的文化内涵外,作者更突出地渲染了他们为了信义打破时空束缚与生死界限的努力,将以死相殉的友谊表现得动人心弦,撼人心魄。在这篇现实与超现实相结合的作品中,艺术真实是与艺术感染力互为前提的。
冯梦龙对小说文体的清醒认识与自觉把握,还表现在他对话本小说文体稳定性的贡献上。编辑“三言”时,他对话本小说的文体作了多方面的统一工作,原本适应现场表演的体制特点在“三言”中得到了整体性地继承与发扬。例如“入话”、“头回”的形式,在说话艺人表演时,除了能显示说话人的见识广博,衬托正话的内涵,同时还能起到静场的作用。对书面读物来说,后一种作用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小说家完全可以如同文言小说那样,直接进入“正话”的叙述。但话本小说的二元结构,确实有助于丰富接受者对小说的感悟,所以“三言”的很多作品都保留或成功地运用了这一形式,如《范鳅儿双镜重圆》头回的“交互姻缘”故事,就很好的衬托了正话“双镜重圆”的故事。
同时,说话艺人表演现场的交流在话本小说文本中也转化为虚拟的对话。由于说话艺术现场表演时,叙述者与接受者同时在场,这必然使得二者的交流具有一定的平等性、适时性,而叙述者会利用这种交流增强情节的感染力。在“三言”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少拟想的交流,如《独孤生归途闹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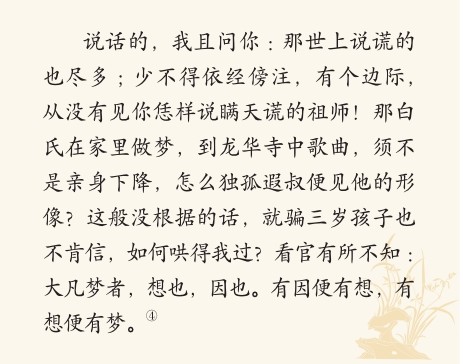
这里的对话就是小说家想象说话表演现象的情形而拟写出来的,意在解决接受者对小说真实性的疑惑,为小说叙述的展开提供了一个合理化的解释。
鲁迅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了“拟话本”的概念,从“三言”的实际看,一方面确实保留了对说话艺术的模拟,另一方面,它们又不仅仅是模拟而已,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确立了更为成熟文体形态,小说家则驾轻就熟地运用这一文体表现新的时代生活,为话本小说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在小说发展史中揭示话本小说的“通俗”意义
在《古今小说叙》中,冯梦龙简要地描述了古代小说的发展轨迹。在此之前,像冯梦龙这样具有融汇古今、兼及文白的小说史观的人并不多。他认为明代小说“往往有远过宋人者”,因为“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⑤正是基于对“不通俗而能之乎”的意义判断,冯梦龙提出了话本小说“谐于里耳”“嘉惠里耳”的重要命题,这是其小说经典意识的一个出发点。
“通俗”有不同的表现与意义,首先是题材应为大众、特别是普通市民所熟悉,接近他们的生活与思想感情。作为经典作品,“三言”的时代特色极为鲜明,尤以直接反映商品经济所带来的新风尚最为突出。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就是一篇现实性极强的优秀作品,它正面描写商人的婚姻生活,表现了商人从现实和人性出发的态度,突破了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作品曲尽人情地刻画了王三巧的心理变化,她与陈大郎的私通,没有被作者简单斥为“淫”或不贞,而是将其作为现实生活中难以逆料却又自然而然的感情需要来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