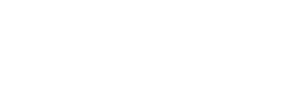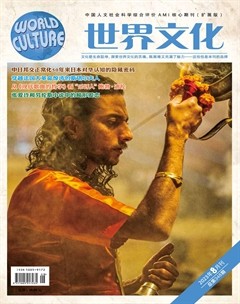作为日本战后“第三批新人”文学群体中唯一的女性作家,曾野绫子(1931— )曾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与有吉佐和子一起引领了日本文坛的“才女时代”。曾野绫子原名町田知寿子,从5岁起便在天主教管理的圣心女子学校学习,并在此度过了17年的学生生涯。受生活环境的影响,她17岁时接受了天主教洗礼,成为一名信徒。曾野在战争期间曾被迫停止学业,前往军需工厂制造兵器,并亲身经历了日本的战败以及随之而来的民主化改革。在日本翻天覆地的社会历史变革中,曾野绫子作为所谓“战中派”作家登上文坛。结合其生活环境及成长经历,好友兼评论家鹤羽伸子认为,家庭、战争、宗教等因素在她的文学创作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曾野绫子出生于知识分子和商人家庭,父亲是庆应义塾大学的高材生,祖辈自文化·文政时代起便居住在江户。家族中曾有先辈于日本桥一带经营当铺,这也逐渐使族人养成了重视季节感的生活习惯以及彬彬有礼、小心谨慎的性格。母亲的祖辈是北陆沿岸的货运批发商出身,沿岸货运业是以海洋为对象的动态商业活动,流动性强。绫子身上融合了两个家族的生活基因:一方面,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小心谨慎、诚恳守信的品性和坚持不懈、孜孜不倦的毅力。这种气质催生了《祭品之岛》(1969)、《那个人的名字叫约书亚》(1977)等作品的诞生,若非在详实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研读并改编,仅凭想象力是无法完成这些作品的。另一方面,她也从母亲的祖辈那里继承了流动性强和无惧起伏的冒险精神。只要工作需要,她便会毫不犹豫地前往印度偏僻地区缺少水电的莱伊医院采访,也会深入毒蛇蛰伏的草丛。她能够忍受臭虫、虱子、40℃的高温和—20℃的严寒,其足迹遍布世界各地。这种充满活力的气质,成为其前往各处实地考察和取材的有力支撑。

说起对曾野绫子个人及其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就不得不提及她的母亲。曾野绫子的母亲酷爱文学,曾跟随中河干子学习和歌,头脑清晰、口才出众。她十分注重对女儿的培养。在曾野年幼时,母亲便委托后来成为国语教育权威的望月久贵对其进行写作指导,至小学毕业时曾野的文笔日臻成熟,并写就了作品《桃源之乡》(1943),虽然只是十余页稿纸篇幅的短文,但此番经历为她日后走上创作之路打下坚实基础。
在外人看来,曾野绫子的人生非常顺利。父亲是公司的董事,她又在田园调布的高级住宅区长大,毕业于上流社会子女聚集的圣心女子学院,大学四年级时与东大毕业的新晋作家三浦朱门结婚。大学毕业那年,她的作品《远方的来客》(1954)入围芥川奖,在文坛华丽出道。从她的经历中很难找到不幸的影子,当时有人称曾野为“幸福的女人”。然而,看似幸福美满的表象下却潜藏着危机—曾野和母亲常年遭受父亲的家庭暴力,这给她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甚至长大成人后仍留有“暴力后遗症”。在部分作品中,曾野对于暴力场景的描写也是其自身经历的一种外显,如《远方的来客》中林奇队长对罗兹中士所实施的暴力行为即是如此。
前文提及,曾野的母親对她的人生际遇和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母亲虽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性,但婚姻的不幸让她有了强烈的趋死倾向。因不堪忍受家暴的伤害,母亲曾两度带着曾野自杀未遂,甚至与丈夫离婚后还企图自杀。上天赐予的顽强生命力使得她逃脱死亡,之后一直与女儿共同生活,直至离世。艾里希·弗洛姆认为,“母亲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恐惧都具有传染性,两者都会对孩子的全面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曾野与母亲在相依为命的同时,也形成了心理学家所谓的“近亲相奸式共生”关系。“所谓母爱,应该是解放所爱的对象的爱,应该是以分离为最终目标的爱,但绫子的母亲一生都无法离开女儿,痛苦不堪。”曾野原生家庭的不幸也孕育了其文学创作的一大主题—亲子关系。这一创作主题在其早期的长篇小说《玉响》(1959)中便有所显现。该作品讲述了在母亲形影不离的呵护下长大的男孩儿,成年后仍无法摆脱对母亲的依恋,于是破坏各种人际关系,最终消失在异邦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