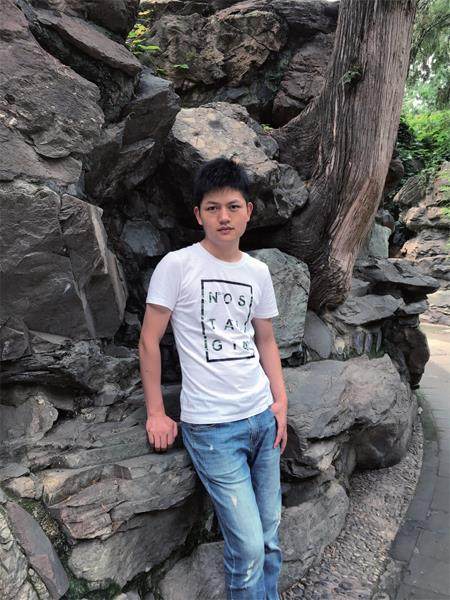
早上九点五十七分,陈衡终于赶到写字楼下,手机连上公司的WiFi,自动打上了卡。在一楼星巴克等咖啡的空隙,孙晓琪发来几条微信,表面上只是单纯地问好,没有其他更亲密的字眼。他心里暗笑,这是孙晓琪内心的那一点儿小骄傲,昨晚大概又梦见了他。孙晓琪说,需要他首先表现出亲密,她才会有相应的反应,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
陈衡打开他常用的那个App,木木美术馆这次乔治·莫兰迪的展览活动被置顶了。他自己是做所谓的互联网运营工作,每次碰到类似的事情,心里都会有一丝不舒服,像是心底隐秘的想法被某些人或者技术偷窥了,更可怕的是,所有人似乎已经很接受这种现象了,搜索过的东西、关注过的商品,甚至是在私人聊天软件里提到的某些内容,总是在“不经意”间出现在另外一款App的页面上。肯定是有什么东西被窃取了,陈衡想。
咖啡好了。他提著咖啡,带着一点侥幸,忍不住点进了这条“不经意”的广告,周日的票仍旧显示的是“售罄”两个字,冰冷冷的。他还不死心,连灰扑扑的“售罄”两个字也要伸手去戳一下,当然是没有任何反应的。他有点儿没来由的气,犹豫着是否删掉昨天发的求票帖。每周就这么宝贵的一天休息时间,连睡觉都不够,何苦还自己求着大老远出门。他看了一下展览信息下五花八门的留言,又觉得纯粹是在浪费时间,大多数时候,他都对App上大量存在的附庸风雅的用户感到失望,很多电影、书籍、演出都被不辨目的地“控评”,跟前几年相比,现在几乎已经不可能从评论里面找到有价值有启发的思考了,更多的时候,他只会参考自己信任的那几个“好友”的评分。陈衡终究没有删掉帖子。
第一次知道“莫兰迪”这个名字也是出自“莫兰迪色”,所谓的“高级灰”和“性冷淡风”,正好契合了当下的流行趋势,甚至连清宫剧里面的配色都跟“莫兰迪”扯上了关系。陈衡第一眼看到莫兰迪色卡的时候就被触动了,那些颜色被命名为杏白、鹅黄、酒红、雾霾蓝、石英粉、橄榄绿、丁香紫、焦糖棕……全都带有一点儿石灰的哑光质感,确实会在第一眼即给人特别的感觉。后来他看了介绍的资料才知道,莫兰迪是在他的画中加入了“灰”和“白”两色去调和,让浓厚艳丽的颜色变成低饱和度的“高级灰”。跟达芬奇、莫奈、凡高和高更这些天才画家相比,莫兰迪要小众得多,真正吸引陈衡的,与其说是莫兰迪独特的色彩,倒不如说是他的生平,跟那些有很多奇闻轶事可以讲述的艺术家相比,莫兰迪完全可以说是平平无奇,一生几乎都没有离开过家乡的小镇,唯一一次出国就是去苏黎世参观塞尚的画展。在图册上见到莫兰迪画的那些瓶瓶罐罐的时候,陈衡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冒出那个很无厘头的念头,莫兰迪要么是同性恋,要么就是阳痿,反正没有男女之间性生活的那种,甚至连手淫的念头都有可能被他给断绝了。陈衡还特地去查过资料,莫兰迪孤单一生,从未结过婚,似乎也没有任何爱情的痕迹留存,他更像是一位生活在欧洲的中国苦行僧。他甚至还真的找到了莫兰迪生前好友对他的评论,“莫兰迪的绘画别有境界,在观念上同中国艺术一致,他不满足于表现看到的世界,而是借题发挥,抒发自己的感情。”陈衡当然不具有专业艺术家的眼光,但是他看着莫兰迪的瓶瓶罐罐,真的从心底里泛出了一些被他自己称之为“温柔的慰藉”这样的东西。关于作品的形式问题,莫兰迪有这样的论述,“我记得伽利略的话:‘真正的哲学之书、自然之书的文字跟我们自己的字母表相去甚远,它们的文字是三角形、正方形、圆形、球体、棱锥体、圆锥体以及其他的几何形。’伽利略的思想支持着我长期持有的一个信念,这个可见世界是一个形式的世界,要用词语去表达支撑着这个世界的那些感觉和图像是极其困难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归根到底它们是感觉,是与日常物体和事件没有关联的感觉,或者可以说与它们只有一个间接的关联,这些事物是由形式、色彩、空间和光线来精确地决定的。”作为一名严肃的(虽然陈衡从未对外如此介绍,但是在心底,他已经把自己归入此类)青年作家,陈衡在莫兰迪的身上找到了一种“榜样的力量”,莫兰迪的艺术和生活,似乎就是他想象中的理想生活,不结婚、不生孩子,像自愿囚禁在少林寺里的扫地僧那样,年复一年去追求某种艺术,不计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