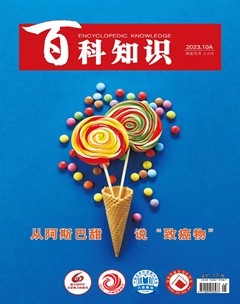处于白山黑水之间的中国东北地区,自然环境适宜,物产资源丰富,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场域。在茫茫历史长河中,东北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创建了彪炳史册的民族政权,绘就了一幅五彩斑斓的民族画卷,深刻影响着东北地区乃至国家历史发展的进程。正如东北史研究开拓者金毓黻先生所说:“东北史者,东北民族活动之历史也。无东北民族,则无所谓东北史,故述东北史,必以民族居首焉。”可见,东北各族人民生息繁衍的历史,是东北地方史中最为重要的篇章。
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
东北地区幅员辽阔,自然环境多种多样。温带季风性气候丰沛的雨水使广袤的平原、山地间水网密布,大片森林、草原为种类繁多的动物群提供了绝佳的栖息地,也为生活在同一片土地、处于相异自然环境中的人类采取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奠定了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多样的自然环境衍生出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并在交流、交往中相互交织,使这片大地蕴含着绚烂的底色。
渔猎文化
东北地区广阔的森林、草原、河流以及蕴含其中的丰富的动物资源,为渔猎文化的滋生供给了充足的养料。辽宁海城仙人洞遗址出土的鹿角制鱼叉清楚地表明,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东北原始经济已由单纯的山地狩猎发展到渔猎并存的模式。
进入历史时期,东北渔猎文化更加丰富。肃慎族不仅制作渔猎工具,还将它们作为特产进贡给中原王朝,《竹书纪年·五帝纪》中就有肃慎族以“楛矢石弩”作为贡品的记载。以渔猎为主的生产方式,要求以此为生者必须掌握充足的狩猎技巧,射箭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技能。生活在长白山北麓以“射猎为业”的挹娄人便有出色的射击技能,《后汉书·东夷传》中形容挹娄人“多勇力,处山险,又善射,发能入人目”。到东汉时期,生活在东北地区的鲜卑人不仅以“弋猎禽兽为事”,还因出产好弓而闻名,鲜卑人生产的“角端弓”以本地异兽角端牛的牛角制成,质地坚硬、杀伤力强,性能较中原弓箭优异许多。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东北部分族群虽然不再以渔猎为主要生产方式,但渔猎文化深深地印刻在了他们的基因当中。辽代,契丹人对狩猎的爱好有增无减,不仅辽朝皇帝的四时捺钵制度始终伴随着渔猎活动开展,契丹民众也将狩猎作为娱乐方式进行“打围”,在不同时节狩猎不同的动物,并形成了一定的时间规律。

狩猎技能还和军事训练结合起来,用以提升军队的作战能力。从女真灭辽到蒙古兴起,再到清军入关,这些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军事行动中,具备优异骑射技能的士兵是无往不利的关键所在,《满洲源流考》中便认为清军“因娴于骑射,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为保持本民族善于骑射的特性,清帝经常前往“围场”进行狩猎,康熙皇帝、乾隆皇帝还会在东巡途中于荒无人烟处挽弓射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