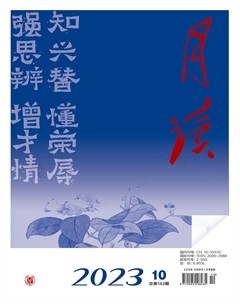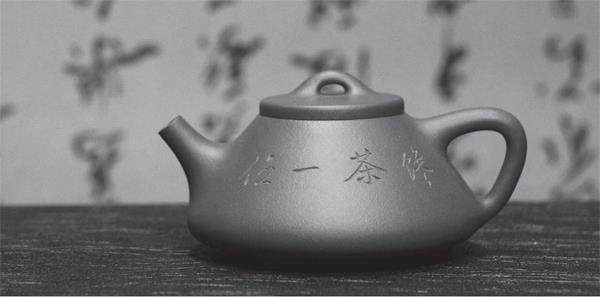
禹贡通远俗,所图在安人。后王失其本,职吏不敢陈。
亦有奸佞者,因兹欲求伸。动生千金费,日使万姓贫。
我来顾渚源,得与茶事亲。氓辍耕农耒,采采实苦辛。
一夫旦当役,尽室皆同臻。扪葛上欹壁,蓬头入荒榛。
终朝不盈掬,手足皆鳞皴。悲嗟遍空山,草木为不春。
阴岭芽未吐,使者牒已频。心争造化功,走挺麋鹿均。
选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众工何枯栌,俯视弥伤神。
皇帝尚巡狩,东郊路多堙。周回绕天涯,所献愈艰勤。
况减兵革困,重兹固疲民。未知供御余,谁合分此珍。
顾省忝邦守,又惭复因循。茫茫沧海间,丹愤何由申。
——〔唐〕袁高《茶山诗》
《全唐诗》中有一位诗人,名下只收录了一首诗。
但是这一首诗,偏偏还就是茶诗。
这位诗人,名叫袁高。
这首茶诗,题曰《茶山诗》。
袁高,字公颐。他生于唐玄宗开元年间,比茶圣陆羽还要年长几岁。袁高于唐肃宗时中进士,后任御史中丞、京畿观察使等职。他为官直言敢谏,不避权贵,屡次上书针砭时弊。袁高并不算一位高产的诗人,而更应视为一位兢兢业业的官员。纵观其一生,只有一首诗歌传世,内容也与他的工作有关。
袁高的工作,与茶有什么关联?您就是翻遍了两《唐书》关于袁高的文字,也找不到只言片语的记载。可要是与茶无关,袁高又为何去茶山?袁高诗中所写,又是哪一座茶山呢?看起来,要读诗之前,题目总要拆解清楚才行。
宋代赵明诚曾在其《金石录》里,根据《茶山诗》及李吉甫《碑阴记》,补正了两《唐书》关于袁高于代宗、德宗朝历官的记载:
右唐袁高《茶山诗》并于頔撰《诗述》、李吉甫撰《碑阴记》,共两卷。湖州岁贡茶,高为刺史,作此诗以讽。高,恕己孙也。贞元中,德宗将起卢杞为饶州刺史,高任给事中,争甚力,于是止用杞为上佐。德宗猜忌刻薄,出于天资,信任卢杞,几亡天下。奉天之围,赖陆贽之谋以济。杞之贬黜,迫于公议,然终身眷眷不能忘,于贽则一斥不复,其奔走播迁而不忘者,岂非幸欤!非高等力排其奸,则复任用杞,未可知也。《唐史》称:高,代宗时,累迁给事中;建中中,拜京畿观察使;坐累贬韶州长史,复拜给事中。吉甫为《碑阴记》,述所历官甚详。云大历中,从其父赞皇公辟,为丹阳令,再表为监察御史、浙江团练判官。德宗嗣位,累迁尚书金部员外郎、右司郎中,擢御史中丞。为杞所忌,贬韶州长史,寻刺湖州。收复之岁,征拜给事中以卒。然则高,代宗朝未尝为给事中,德宗朝未尝拜京畿观察使,其贬韶州时,实为中丞;而其为中丞与湖州刺史,《传》皆不载。今并著之,以证《唐史》之误。
袁高,曾经为李栖筠的下属。李吉甫,是李栖筠之子,因此他所补的内容可信度应该很高。由此可知,两《唐书》关于袁高的记载,最主要就是漏掉了他担任湖州刺史的经历。
袁高“寻刺湖州”,主要是因为得罪了权臣卢杞,可算是贬官了。而后“征拜给事中”,则是因为唐朝刚刚平定了朱泚之乱。唐德宗认识到袁高的重要性,因此再度重用袁高。这些内容,都在这首茶诗里有所体现。随后的正文中,我们再慢慢拆解。这里着重说明一下,湖州在茶史中的重要性。
在唐代茶史中,湖州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湖州常年贡茶,起始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据北宋钱易《南部新书》记载:
唐制,湖州造茶最多,谓之“顾渚贡焙”,岁造一万八千四百八斤。焙在长城县西北。大历五年以后,始有进奉。至建中二年,袁高为郡,进三千六百串,并诗刻石在贡焙。故陆鸿渐《与杨祭酒书》云:“顾渚山中紫笋茶两片,此物但恨帝未得尝,实所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