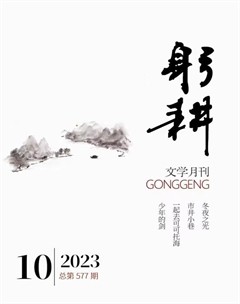谷禾简介:
谷禾,本名周连国,1967年生于河南农村。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写诗并发表作品,著有诗集《飘雪的阳光》《鲜花宁静》《坐一辆拖拉机去耶路撒冷》《北运河书》《世界的每一个早晨》等多部,部分作品被译成英、韩、西班牙等语种。获华文青年诗人奖、《诗选刊》最佳诗人奖、扬子江诗学奖、刘章诗歌奖、《芳草》当代汉语诗歌双年十佳、扬子江诗歌奖、《长江文艺》双年奖、屈原诗歌奖、陆游诗歌奖、草堂诗歌奖等奖项。现居北京。
谷禾从1980年代末期开始诗歌写作,始终保持强劲的写作势头,迄今已出版《飘雪的阳光》《大海不这么想》《鲜花宁静》《坐一辆拖拉机去耶路撒冷》《北运河书》等多部诗集。谷禾把他最初写作的十年称为“写作学徒期”,这固然可见他的谦逊,也可见他的写作是有备而来,并非出于对诗歌单纯的来源于兴趣的热爱,而是把写作依存在处理生命体验的深度上。一位真诚的写作者往往有持守的耐力,他会把写作近乎本能地聚焦在自己生命体验最深层的沉淀上,由此获得一种对称于自己生命体验的内在视野。这实际上是对一位写作者理解生命何为的检验,同时要求写作者把自己的生命困境化解在最纯粹的诗性体验上。写作对于写作者的价值就其本质而言,是纯粹精神性的,是对于美的一种近乎固执的守望,而非物质的暂时替代物,要求写作者尤其是诗人,在对自身的观照中焕发出一种全新的无限趋近于美的憧憬。谷禾无疑是一位真诚的写作者,从他的写作历程来看,他有一种相当坚定的持守,他的写作始终在乡土与故园的怀抱中凝聚一种趋向于美的眷恋。
从谷禾诗歌写作的题材、主题和路径来看,把他定位为“乡土诗人”或许有几分道理,但显然不能含括其创作的复杂性。诗人伊沙说,“有一段时间,我曾经认为谷禾是中国最好的乡土诗人。”⑴这一判断可能不无争议,却也大致符合谷禾1990年代诗歌写作的实际情形。谷禾的诗歌写作确实是把乡土作为“根据地”而展开的,其写作题材有其内聚性,乡土是其写作的聚焦点,但其写作的宽幅却是不断延展的,并未局限在乡土的视域之内。这与谷禾的生活经历有关,也与其诗歌的想象方式有关。谷禾出生和成长都在乡村,大学毕业后,在故乡淮河平原深处的一个小镇教书,谙熟故乡的风景人物、历史沿革和乡村习俗,对乡村土地生长出来的一切事物都充满好奇,他在“写作学徒期”的写作就得益于故乡风物的滋养,往往具有鲜活的乡土气息。但他的早期写作又充满奇异的幻想,在他的笔下,故乡的风土人物并不是匍匐在写实的窠臼之中,而是带着想象的灵动,显示出一种特别的敏感于长期乡村生活的审美情趣。谷禾在故乡小镇的十年写作应该是在寂寞中度过的,偏居一隅,文化环境闭塞,从故乡出走似乎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或许也是命运使然,要把诗人带入到“生活在别处”的离散状态。对诗人谷禾来说,这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故乡的远离却是另一种形式的皈依。这不是放逐和流放,而是对故乡另一种形式的唤醒和回归,同时也是超越自我的局限,把自我的丰富性激活在更具内在生命冲动的诗性创造上。
1999年秋天,谷禾决定来北京闯一闯,先是到鲁迅文学院读书,后来辗转到一个杂志社工作,直到今天。应该说,谷禾生活状态的这种变化对其写作的影响是重大的,谷禾的“写作学徒期”至此结束,他作为“乡土诗人”的符号性面具也随之变得丰富和复杂起来。对一位成熟的诗人来说,他的创作因各种机缘和出于艺术探索的动力而变得丰富和充满杂色,也许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也有利于其创作真正敞开具有个人独特性的视野。谷禾说,“我坚守那种忠实于自己的生活和内心的写作。希望我写下的分行文字可以成为个人生活和时代的见证。”⑵新世纪以来,谷禾的写作确实具有见证时代、分辨时代的意味,也具有在见证时代的过程中不断分辨自我的意味,另一方面是在见证和分辨中不断凝定自我风格的可辨识度。
谷禾在《一夜家乡》中写道,“家乡啊,我的牵肠挂肚/就像槐树上的鸟巢/捧起满树星光,又尽数漏掉”,诗人写自己的归乡感受,诗中交织着温暖与寒凉的情感变化,记忆已不复完整,家乡也已不复往日的样貌,在诗人对故乡的牵肠挂肚里包含着复杂的情感。这是诗人长居北京之后“返观”家乡的情感反应。“一夜家乡”,表明诗人来去匆匆;诗人在夜里辗转反侧,“我睡去。醒来。窗帘动荡/摇晃,辗转的疼/沿着雨线爬上爬下”,表明诗人不忍匆匆离去。此诗颇能代表谷禾長居都市之后对故乡情感的微妙变化,另一方面也包含着诗人观察视角的变化。对照他的《我爱》,似乎可以看得更清晰一些。谷禾如此写道,“我爱过平静的乡村/——炊烟,槐花,起伏的麦浪,/热烘烘的牛粪”,定居都市之后,他也爱“水泥,钢筋,尘埃滚滚,灼热的/汽车尾气。闪亮的钢轨……”,甚至也爱都市的“浮华、冷漠、孤单/夜幕下的灯红酒绿”。显然,在谷禾的诗中,包含着一个城乡对照的视角,包含着在复杂的现代性情境中如何安置乡愁的文化命题,再往大处来看,实际上也包含着一位诗人在现代性情境中复杂的文化选择。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是返乡,惟通过返乡,故乡才作为达乎本源的切近国度而得到准备。守护那达乎极乐的有所隐匿的切近之神秘,并且在守护之际把这个神秘展开出来,这乃是返乡的忧心。”⑶谷禾的返乡大概具有双重意味,一是作为一个定居都市的“乡下人”返归故乡,在现实情境中返回与“本源”的亲近,故乡并非只是一个想象中的心灵栖所;一是作为一个诗人的“精神返乡”,返乡映照着寻找诗意栖居的心灵本真性,里面隐含着文化乡愁。需要注意的是,谷禾并没有简单地以“乡下人”自居,没有对现代性持一种简单的批判性态度,而是从自己的生命感受中呈现出城与乡在现代性情境中的复杂图景。城市处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乡村也并未停留于世外桃源的状态,而是二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依存性。尤其对谷禾这样一位从乡村来到城市定居的诗人来说,他的体会尤深。
尽管谷禾的生活轨迹并非他所独有,可以代表同时代诸多诗人的共通性境遇,但仍然有其独属于个人的特殊性。具体地说,谷禾的出生和成长之地周庄属于淮河平原,地处中原内陆,他最初的诗性想象带有中原内陆地区天高阔远的特点,他的乡土记忆也蓬勃着中原内陆地区特有的自然物候信息和文化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