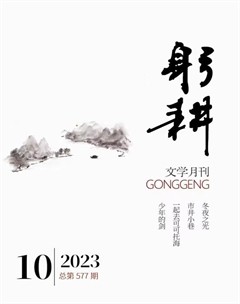新年曙光的冉冉升起,昭示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业已成为过去,当我们回望新世纪汉语诗歌,却看到它似乎并没有迎来“隨时间而来的智慧”,迈入宏阔的沉潜状态,相反却陷入了更普遍性的“影响与焦虑”的涡旋。这样的“影响”通过线上线下的联动,其常态化既表现为协同场域的热闹和喧哗,也表现为不同语境下和相同语种的写作者之间频繁交流所带来的虚飘。在他们看来,当下汉语诗歌写作至少已经取得了不输于世界上任何语种诗歌的艺术成就,属于它的大诗人已呼之欲出或正在路上。一批怀抱更大雄心的处于中年写作状态的诗人,开始自觉地回溯悠久的中国古典诗歌传统,试图认祖归宗,从中国古典诗歌的深井里找到当代汉语诗歌的源头和镜像。令人不解的是,读者并没有看到这样的影响通过良性的继承、吸纳和发展,为当代汉语新诗写作提供出扎根和生长的崭新沃土。而由此带来的焦虑却是,创新和超越仍只是一种美好愿景,更多写作者荫庇在“大师的阴影下”和同辈的“影响”里,乐此不疲地相互模仿和双手互搏,他们泥沙俱下的诗歌文本里当然也有各自粗糙或精致的生活,却鲜见对日常生活的独特观察和精确把握,鲜见运用个人经验和想象力完成对日常真实的洞悉和穿透,更鲜见对“日常生活和现实历史的奇迹”的深刻揭示。
在此我们看到,在从自己身上和身边找到渴望中的大诗人之前,越来越多的清醒者看到了众声喧哗下掩藏的当代汉语诗歌的内部危机。紧迫感和使命感促使他们反复提及到了最伟大的前辈写作者杜甫,并尝试从杜甫身上找到问题的解决之道。
没错,作为中国古典诗歌书写的集大成者,其前人给予了杜甫最丰富的诗歌营养,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杜诗中却很少有可以单独拎出来作为个案解析的存在,而是分化成了无数的小我,隐匿在杜甫使用过的古老词语里,以至后世读者阅读的时候,随处都能找到陌生或熟悉的自己。诗人哨兵不无感慨地这样写道:
“公祭警报//一声紧过一声,也没能把那一片残荷/催出花来。我越老//山河就越像杜甫,每一爿败叶/都是残骸,每一根枯梗//都是遗骨。而公祭警报/一声紧过一声,一片残荷//坐湖,就是一群杜甫/围着各自的暮年,遥跪//一样的长安乱” (哨兵《清明公祭,闻警报志哀兼与残荷论杜甫》)。
国有难,思杜甫,但是,当山河都是杜甫,杜甫活在每个人的身体里的时候,杜甫何为?难道就只剩下“围着各自的暮年,遥跪/一样的长安乱”吗?
当然有说不尽的杜甫,但当我们明确“杜甫唯一可以确定的特性就是他的丰富性”时,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这样写道:“在杜甫的时代,诗人们已经形成了统一的、无区别的诗歌特性,以对抗题材传统有力的离心影响,而杜甫却体现出多样化的才赋和个性。杜甫是律诗的文体大师,社会批评的诗人,自我表现的诗人,幽默的智者,日常生活的诗人,及虚幻想象的诗人。他比同时代任何诗人更自由地运用了口语和日常表达;他最大胆地试用了稠密修饰的诗歌语言;他是最博学的诗人,大量运用深奥的典故成语,并感受到语言的历史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