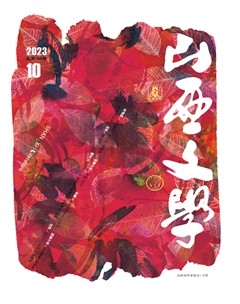农历六月初七。
下午四点二十六分。
一路沿平西大街往南开,大约半个小时车程,会途经一段崎岖的土路,路过一处野坟,零星的几户人家以修车和经营小饭店为生,最后随便找个空地停好车,匀速往西步行十五分钟,就是今天故事的发生地。
故事主角登场。
一只颜色杂乱的猫。
阿里被手稿囚禁在阴暗的工作室几个月,跟只炸毛刺猬似的,挎着脸钻出来时,发现了它。
老话说“鸡来穷,狗来富,猫儿来了要开大铺”。
阿里坐在冰凉的台阶上抽烟,脑子里一溜烟冒出这么一句话。
抬脚抖掉脚背上的蚂蚁,捏住眼镜的鼻托,朝镜片哈了一口气,然后用衣角蹭掉镜片上的墨水痕迹。
阿里麻利地做着一系列动作,脖子上的青筋一会儿明显,一会儿又看不见,嘴巴里干得仿佛十几年没下雨的土地。
“热死爷爷的鬼天气!”
阿里眼睛瞪得溜圆,前倾脖子,好让汗水滴在地上,烦躁地冲着那只猫龇牙咧嘴。
那只猫从一人高的绿色垃圾桶后边一跃而出,落地无声,轻巧地像片树叶,体形却像是一堆发过头的玉米面团,身体一歪瘫在一辆黑色大众车旁边晒太阳,胸口起起伏伏,不时起身弓着背舔舐后腿的毛。
阿里的目光来来回回几次,最终还是被它吸引,捞起脚边的石子干干脆脆地甩过去,石子不大,正好敲打在它的尾巴根儿上。
它嗷地叫了一声,梗起脖子眯眼打量阿里。
阿里完全不把它放在眼里,打了个哈欠,把抽了一半的烟扔在地上,愤愤碾上几脚。
“老陈那个狗东西。”
阿里忘了为什么要骂那个老陈,只隐约记得他做了不小的坏事,和自己在街面上打了一架,还惊动了派出所。
派出所的同志态度很好,也很有耐心,批评教育了两个多小时。
从派出所出来,老陈是打了辆摩的走的,阿里则去了趟卫生所。
卫生所的小姑娘已经备好了阿里需要的三服中药,装在塑料袋里,见阿里悻悻然,不由得多嘴问了缘由。
阿里直说是自己不小心摔了,付了钱,拿了药,急匆匆地跑了。
“狗东西。”
阿里往地上啐了一口。
那只猫慢腾腾往这边挪了几步,屁股一沉,坐在柿子树下,一言不发。
有那么一瞬间,阿里对这家伙竟然有种似曾相识的亲近感。
但,很快烟消云散。
“你是谁家的?”
阿里问。
那只猫歪着脑袋,满脸疑惑。
“你也没人要啊?”
阿里又问。
那只猫不再回答,干脆躺下了。
阿里是个性格古怪的人,每个人都这么说。
不过,他自己倒无所谓。
阿里工作的地方在一座破旧的老式小二楼的一楼东拐角,单独隔出一个小房间,灰墙红木窗,一张茶几,一张单人床,一个军绿色暖水壶,地上到处散乱着废弃手稿,门把手锈迹斑斑,倒贴的福字早已从大红色褪成了粉色。
这座小楼听说是民国时期,某位人物给他情人住的,情人病死之后,那位人物就再没有来过,几年以后转卖给了一个商人。
阿里打心眼里瞧不起那位主儿,好歹是个念想儿,就那么随随便便卖了。
距离阿里工作不远的地方有一所职业学校,名字很长,和餐饮有关,据说是省里定点培训基地,哪年来着,还上过电视,说是出了个获得国际大奖的牛人,长得像老家村里的妇女主任。
若是得空守株待兔,还会见到三三两两的学生穿着白色厨师服,抬着硕大的桶,有时还会拎一个大勺,嬉笑着从一个校门到另一个校门,那个桶阿里只在商场接水的时候见过,密封性很好,容量也不小。
他们就像这只猫,总是突然出现。
不巧的是这个时候的阿里烦透了。
“老陈,狗东西。”
他语气似乎缓和了些,接着,哈哈大笑,摸出手机,上下翻看通讯录,并没有找到一个姓陈的。
也许是个绰号,也许是和陈同音不同字。
阿里总是这样。
打小,妈妈就总和旁人说,他有做艺术家的潜质,连睡觉都要抱着铅笔,后来考上美院,却差点因为挂科拿不上毕业证。
阿里朝学校的方向看过去,大门紧闭,门卫大爷背着手在门口溜达,见阿里看他,赶忙转了个方向。
阿里亦没有开口喊他,只是把眼镜摘了,嘴里不住地念叨。
“度数又高了。”
天气闷热得令人作呕,无风,像是身处蒸笼里的肉包子,不住冒着蒸汽,灰蓝色短袖上爬满一道道白色的汗渍,后背一阵阵瘙痒太刺挠,阿里背手去抓,够不着,肩膀“咔咔”响了两下。
这动静吸引到了那只猫,好奇而又崇拜地望过来。
“起开!”
他说。
那只貓只顾瞥了一眼,鼻翼下挂着亮闪闪的水珠子。
阿里当即就拉下脸,绕过它,时不时回头,确定它没有搞偷袭,才大胆地站在另一处栏杆旁继续抽烟。
大拇脚趾头泄气地越过深棕色皮凉鞋底,垂到地面,干裂的嘴有节奏地吐着烟圈,油糊糊的头发一缕一缕贴在头皮上,整个脑袋远远看上去像极了个白绿相间的熟透了的甜瓜。
阿里觉得此时此刻的自己潇洒极了。
“老陈到底是谁呢?”
阿里看着烟盒发呆。
忽地想起了婷,一个身材高挑,住在高档小区十二楼,在一所大学当班主任,长得很像高圆圆的女孩子。
北方的气候干燥,她的皮肤却格外的好,笑起来甜腻腻的。
阿里绞尽脑汁从脑子里搜罗了一通,想到了红豆糯米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