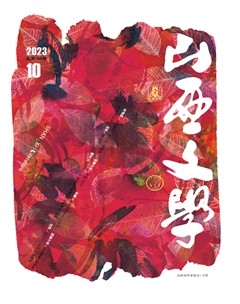一
乡医院曾在鲍墟村最繁华的东西大街上,路南那个面北的拱券式门楼里,大门虽已消失,门楼的威仪尚在,以致门楼砖缝间生出的杂草都比别处粗壮。我在医院工作时,那里已经成了邮电所和信用社所在地,对面依旧是经营油盐酱醋日用百货的乡供销社,我纳闷乡医院为什么搬迁到人宅寥落的村北。
鲍墟是个古村,比较方正,它弯弯曲曲的街巷中,已没有明嘉靖《蠡县志》中所载蠡县八景中的 “鲍墟龙渊”。站在土墙砖墙林立的村街,放眼望去,玉米秸和棉花柴依满了墙,棉桃龇开嘴儿,露出点点白絮,任风扯。这里的土质具有潴龙河下游河畔的特性,沙多黏性小,可很多人家的院墙是用泥土夯成,孙犁先生的作品中称为“立土”。青砖房子居多,红砖房大都为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所建,一明两暗,或三间两跨,平顶。与孟尝村不同的是,院子都很大,果树昌荣,菜地油绿。
我曾在鲍墟读初中,三年穿村而行,上卫校时借读刘素娥老师的《蠡县志》,才知道村子有“鲍叔故里”之称,传说来自春秋时期,与之相连的建筑早没有一丝痕迹,只有记载。在南鲍墟村西南,有一列耸起的东西向土堆,隐约有八座坟,埋葬着白马连八名抗日英烈。前不久,被时间遮蔽的烈士事迹登上了央视的《国家记忆》栏目。
父亲说,老卫生院在董家串连呀(音,约为民国时建筑,门洞性质,没有院子,有立柱,有台阶,比较豪华)。
父亲曾在鲍墟公社社办厂待过几年,竟然不记得我说的卫生院,而我从来没听说过董家串连。可是父亲说得有板有眼——董家串连在商店西边。正是西大队董姓人家聚集的地方。我越发如蒙在鼓里,急切地想知道。
我所认识的乡医院人中,资历最久的宋医生和六叔已离世,苗医生多年没联系,也只有常水叔和崇伦姐能证明。
常水叔和孙子杨阳在肃宁县城开诊所,电话打过去,常水叔正因疫情封闭在家中。话题一打开,竟让我吃一惊——上世纪六〇年乡医院还曾在常水叔家办过,借用他家的西屋和中药橱。那时常水叔才上小学。当时的院长是戴卫华,还有一任院长姓赵,有个司药叫关景銮,是李岗人。信用社那地方做卫生院时,院长是王长峰,刘佃庄人,老革命,毕业于白求恩卫校……董家串连那会儿好像叫卫生所。
这个七十多岁的人,声音和精气神一点不老,思路清晰,关于我们共同的乡医院他滔滔不绝……
至于药斗子中草药的排序,常水叔说上下左右分别属南北东西,对应朱雀玄武青龙白虎,用数字表示上下左右就是一二三四。老人家懂中医学和《周易》。
乡医院有两组高大的药橱子,立在药房的北山靠东墙处,枣红色,每个抽斗都是铜拉手,坏掉的用布条替代,摩挲多的地方连枣红色都磨了去,包浆愈加清晰浑厚,铜拉手的光亮晃得出人影来。常用药一般在中部,淡颜色和亮闪的铜拉手在药橱子上形成一个隐约的圆。中药的名字像花名册,四个一组上下左右排列着。酸甜苦辣咸五味混合的药味,让整两间长的药房都弥散着特有的芳香。因为对中草药感兴趣,护士工作做完,就跑到药房帮着抓药,那些草本的木本的,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海陆空的珍宝们是那样吸引我。比方作用于三焦的黄连、黄芩、黄柏,比方有大名小名的昆布、莱菔子、芡实,很多名字有意蕴有故事有传说,食物也是药物,贝壳也能治病,有着大自然的神秘和机理,令人着迷,更毋论其意想不到的产地、形状、性味归经、配伍禁忌了。我曾在其他文章里写这些草木的精灵,忍不住记录。当时还跟同事安一起背汤头,什么十八畏、十八反,其实我俩都没有处方权,背诵这些草药歌就是因为喜欢。安坐在床頭,手按着桌子上的《方剂学》,笑眯眯地说,背半天也没用,咱们不会号脉。
常水叔说借他家中药橱,我猜他中医世家。
常水叔说:“家谱记载从明代几乎没有断过,可惜文革时家谱毁了。我父亲是 ‘秀才’,读 《五经四书》《周易》,也懂点奇门遁甲。”常水叔的爷爷本姓袁,过继给杨姓舅舅,与袁家也亲近,杨家这几户都是常水叔爷爷开枝散叶的结果。袁家祖上行医留下一个故事,袁家祖爷爷艺高人大胆,但是犯了致命的错,连累了两条人命。发誓再也不坐堂,他赌气是为自己的医术讨说法。临终也曾告诫后辈不以行医为生。
三百多年的故事,肯定具有了荒诞性和传奇性。信息时代,没有人会活在传说里,事实是,望闻问切这门医术留在了杨家,治病救人的一些传奇也在杨家延续。
建院年份还是不确定,却初步了解到,建这所乡医院的院长是侯良臣,我的脑海一下子跳出这个高鼻子老头儿。常水叔说侯院长有三个得力助手——擅长儿科的丁医生、妇科苗医生、药房宋医生。这也是鲍墟乡医院在各乡医院中驰名的原因。
可悲的是,侯良臣院长最后在商业系统某商店退休,那时退休金不归社保局,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商店职工开支都难,他的退休金更成问题。他常常来乡医院,冬天戴着一顶褪色的遮檐蓝帽,袖着手,坐在火墙边,一天一天像上班似的。
接任侯院长的叫马启瑞,蠡县林堡人。第三四任院长我认识——第三任何院长,定州(原定县)人。第四任刘刚院长,潴龙河对岸随东村人。
二
从我的宿舍出来,目光先是被柱子般的大泡桐阻挡一下,而后穿过空旷的院落,对角望过去,是乡医院新修的大门——数十根手指般粗细的钢筋焊接的栅栏门,风随时可以进出,甚至被狗追急了的鸡,也能从栅栏缝里挤进来。红砖院墙比以前高出近一半,但并没能拦住风水,令这个医院强似别家,跟当时的所有人一样,家里没有积面兜里没有积钱。
门开在西南,风水里的西南门,这在常水叔眼里具有拯救的意义。
原本因季节或荒芜或芳草萋萋的半边院子,一年年上演着驱逐与占领的舞台剧。立足院子中土井旁端详,大泡桐种成东西一排偏东居北,槐树占据东南两面,西面院墙有两棵枝枝丫丫住着麻雀的大杨树长出个喜鹊窝。曾踞其下的男女厕所,移到了东南角。最主要的变化是,半个院子成了菜园。房屋及结构实质上很普通,谈不上美不美,砖是红,砖与别处无差,不同之处是房屋较平常人家高大,人字顶,铺着本地罕见的屋瓦,瓦也是红的,遇到雨天,雨水经常绕过屋瓦跑到檐下来,淅淅沥沥滴到床上。这样的房子属于比较简陋的公用房,在建筑学范畴没有地位,与传统的建筑格局更没有关系。
大门那里的变化,是常水叔来乡医院后的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