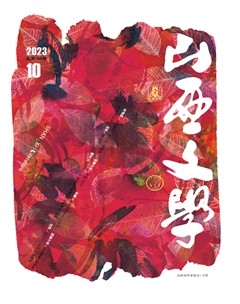编者按 :近期去世的义夫(孙思义)先生,是山西“山药蛋派”第二代作家群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位骁将,运城市重要作家代表之一。1950年代中后期,他以《两个李老头》《羊胡爷爷》等作品引起文坛注目,1960年代前期,又发表短篇小说《老贫农的来信》等作品,集结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红日当头》,并以优异的创作成绩,先后参加了《人民文学》编辑部举办的“读书班”,和1965年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新时期以来,又以《小说选刊》选载、荣获山西文学奖、入选《1984年短篇小说选》的短篇小说《花花牛》重新亮相,佳作不断,《老古学歪记》获得首届赵树理文学奖获奖,并集结出版了《义夫短篇小说集》,享誉文坛。
我们特刊发王西兰、李云峰两位作家的文章,以示追念之情。
义夫老师去世了。作为与义夫老师结识几十年,并得到过他关照教诲的后辈学生,我心里的悲痛,是难以言说的。
义夫老师享年88岁,我认识他已经51年。要说我最早知道他的名字,读过他的作品,还不止51年。我上初中时,学校就我一个订了一份《火花》杂志。有一天,在新来的《火花》上,我读到了一个短篇小说《红日当头》,作者叫义夫。这是我读到义夫老师的第一篇作品,义夫这个名字我也牢牢地记在心里了,只是感觉这个名字怪怪的。读着小说《红日当头》,那让人倍感亲切的乡土语言,那引人入胜却也仿佛熟悉的人物故事,都让从小喜欢文学的我如醉如痴。同学们都出去活动了,我还在教室里反复阅读,那天的晚饭好像也没有去吃。
第二天刚好是星期五,我们那时候每周五都是作文课。作文的命题已经忘了,只记得我学着《红日当头》的语言风格写了一个故事,写的什么内容也忘了。那一段日子我们语文课老师请假了,由一位管后勤的杨老师临时代理。杨老师平时主要带领我们参加劳动,栽树呀,除草呀,打扫操场呀……要是清理厕所,学生要轮流抬尿桶,他在一边认真监督。谁抬过了,他会给一个纸条,上面写“尿一桶,杨XX”。学生们捣蛋,背后就叫他“尿一桶”,很有些鄙薄的意思:他一个管“尿一桶”的会教语文吗?没有想到,下一个周五作文簿发下来,我的作文批了一个大大的“优”,红得耀眼,而且末尾还有批语:“这篇作文写得生动活泼,语言有乡土气息,人物也形象鲜明,是一篇好小说。”
啊,我可亲的可爱的可敬的“尿一桶”杨老师!您真是有一双慧眼呀!您竟然确定我写的是小说!
——我当然写的是小说,我是学着《红日当头》写的呀!
可以说,那时候我已经开始结识义夫老师。到现在,已经有60年了。
1972年10月,山西省召开了“文革”后第一次文学创作会议,运城地区有八位代表参加,李逸民、义夫两位是领头的,还有草章、旭林、恩忠、超万等几位老师,幸运的是,我这个毛头小子也忝列其中。我自然就正式认识了义夫老师,知道了他的真实名字叫孙思义。
这以后运城地区的创作会,几乎每次都会通知我参加,我和孙思义老师也就越来越熟了。除了会议上学习讨论,私底下也和他说说《羊胡爷爷》《一个老贫农的来信》等等具体作品,甚至还要聊一些家常话。什么“荣河谢村”呀,什么“七十二争立碑为证”呀,都是他给我说的。熟悉到这程度,我就可以问问压在心底的疑惑了:您的笔名怎么起了那么两个怪怪的字呢?义字和夫字连在一起算是什么意思呢?听了他的回答才知道谜底很简单:原来孙老师当年上的大学是北京外语学院,学的是俄语,每天说的人名都是“瓦西里耶夫”“乌里扬诺夫”,他也给自己名字加了个夫,就叫“孙思义夫”。这简直太意外了!孙老师竟然上的是北京外语学院!平日里他一身黑棉袄,系一根布裤带,穿一双家做的粗布鞋,说一口土里土气的荣河话,原来是见过大世面的啊!
一两年后,记不得具体时间了,也忘了哪位编辑老师有约,让我给《运城地区报》写了一个小短篇《黄河儿女》。